突然间想奶奶了,不知觉两眼已湿漉漉的。我总感觉到家乡的天空比外边的蓝,很蓝,很高。暮春的阳光下,一棵参天的白杨枝盛叶茂,绿绿的树叶就像刚出水的芙蓉,丰满的让人不禁遐想。老家的美在今天并没有带给我惬意和留恋,我的心在疼,我在送我的奶奶,我送我奶奶入土为安。奶奶八十五岁。奶奶的去世一直让我感到亏心更让我
说儿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财迷一点都不过,他对钱的渴望和拥有不亚于黄鼠狼对小鸡的青睐。说他是有经济头脑,不如说是个十足的财迷。儿子对钱的拥有刚刚表现,以前他从不摸钱。儿子在过周岁时正好十个多月,已经歪歪斜斜的走的很好了。按当地风俗,周岁这天要在院子里摆张矮方桌,桌子上放一百元钱,一个馒头,一个算盘,一本书
村里的人包括村长谁也不会想到多年杳无音讯的大狗能在这个时候回来。回就回来呗,主要是开着车回来的,而且那车还是名车,后来听乡长说的,大狗的车叫奔驰,外国的,贼贵。大狗的小名叫够蛋,村长都这么喊大狗,管大狗的爹叫老狗,由于家里很穷,连四邻八舍都不拿正眼看待。老两口就这么大狗一个儿,都很大了还抹鼻子,弄的
入伍的第二年得知村里的老虾死了,我好一阵兴奋:我最恨的人终于死了,而且是不得好死的,正如我十二岁那年和他急眼时咒骂他那样“冤枉好人不得好死”。不知是应了天意还是该他如此,长食道癌死了,兴奋之后继而心痛,毕竟老虾死时不算年长。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往事充满着硝烟的气味(好事都忘了),常常受人欺负回家还要
新世纪的第一个三月初三,北风狂吼,瑞雪飘飞。也就是这一天,我的舅舅,我唯一的亲娘舅伴着这漫天的舞雪走完了他忙碌的一生。知道这个消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非常的痛心,太突然了,临终也没有见上一面。弟弟在电话里说舅舅是被自己饿死的,他不愿连累他的亲人们。母亲兄妹六人,舅舅是我们的唯一。或因我们兄弟三人自小就
总是感觉干我们出租行业的最辛苦,为了多挣几个钱,担着那份亲人的牵挂常常在风雨中穿梭,在严寒酷暑中等待,为了多挣几个钱,又常常早起晚归,披星赶月常常以马路为家。直到遇见一件事,那种让人歌泣的真情,才让我觉得我们的辛苦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直至今日,想起那个被母亲称为傻子的人带着母亲打工的事,我的眼还是潮露
我这个破儿子,烦的俺贼够贼够的,人不大,话不少,说出的话笑破肚皮。要问儿子你几岁了。四岁半了。再问儿子你几岁了,快五岁了。又问儿子你几岁了,儿子就来劲了,问什么问啊,再问也没有五岁,别问了。媳妇上班的公司里要举行运动会,职工自愿参加比赛,大奖200元,参赛者都有奖,一人一个瓷杯,陶瓷的,一块钱能买两
第一次见到母亲的苍老是在我当兵后第一年回家探亲时发现的。当兵前,朝天在父母面前摇来晃去的并不感觉父母的容颜在一天天的变,也感觉不到那份亲情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要走,才知道这个家是我的牵挂,最难舍的是母亲。离家那天,母亲泪水涟涟却不敢送我去远。那一刻,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涌在心头,不觉间眼泪婆娑又不
岁月悠悠,往事悠悠,我思忖着那个大雪飘飘的冬季。皑皑的白雪,甜甜的歌声“你那里下雪了吗,面对孤独你怕不怕……”我便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心境又把我带到那个有山有水有那支歌的小山城。这支甜甜的歌本是周冰倩唱的,但我第一次听到却是一个女孩唱给我的。许是与她相识有雪的缘分,雪始终在下,每次都把大地裹得厚厚的银
那年因业务与老板去了一次北方的沿海城市驱车来到东城,办完业务上的事,对方老总挽留我们逗留几天,要我们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看一看这里的风光。这开放的城市就是牛气,街道整齐,霓红闪烁,却让我感受到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经济发展。第二天去西城办点事,临走对方交代,中午设宴等候。在西城碰上老板的几个朋友,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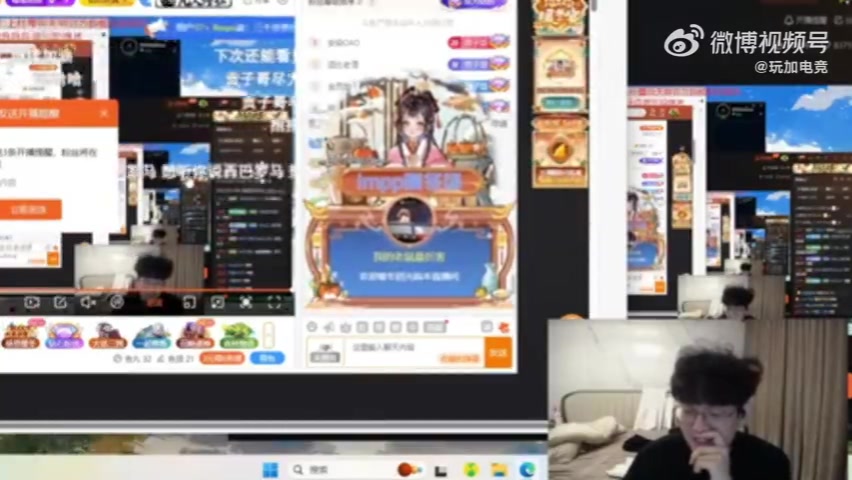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