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漆着大红色的城门外,仰望着青灰色的城墙。我终于来到了这座城,梦里神往的地方,他们叫它京城。回望我走过的路,以及那千里之外的故乡。几个月里,颇多艰辛颇多酸苦。我住过破旧的庙宇,睡过古老的长街,在高原差点窒息,在荒漠差点丧命。每每当我遭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个人,那段时间她是我活下去的唯
我站在我的小木房旁的海滩上,望着面前的大海,原以为我能站到永恒,却站成一座疲惫老人的雕塑。也许,我老了。不老,我怎么会住在这里,还这样活了二十年?海风肆意地削着我的脸,削成一个铅笔画上的人,眼神坚定,额头犀利。夕阳不只染红了西方的天空,我面前海水的颜色也变成了血红色。往事,像漂在海面的落叶被卷进巨大
自由飞翔三天后。下午。老校门外的公交汽车前。影与苗。“你约我出来做什么?我问你,你还不说,搞得那么神秘。”苗看着346公交车说。“石头,和我一起开始一场冒险吧!”“什么冒险?还是不明白。”苗疑惑的说。“公交车冒险,”影见苗还是不明白,“我们随意登上一辆公交车,再随意下车,无目的地,只求冒险过程的刺激
我就是一个疯子那晚之后,真没去找苗。苗因这段感情身心俱疲,真自然对它没兴趣了。一个对爱不忠的人自然不会在乎爱情世界里的另一个人。就像一个赏花者是不会关心赏花后花的死活的。因为有养花人的存在,养花人会照料花的。苗和影一样坚强,伤的再重也不会说痛。能说出来的还不能忍受吗!说不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伤。陷入爱河
爱,就不择手段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有的是萧瑟的秋风,令人瑟瑟发抖的风。月光被冻结,流不到渴望光亮的大地,于是大地呈现黑色,而这黑色下容易滋生的是暴力与邪恶。老校门外的世界,由于没有多少人的呼吸,似乎更冷。那儿风吹得更凶,能够听到树叶抖动的声音,比铁锯锯木的声响还添几分刺耳。门外的路灯,年久失修,一直
陌路人,你好这几天,影的兄弟帮揽了几桩生意,多数关于情感纠纷,影本不打算亲自去处理的,苗的“背叛”,他的心至今都没真正放下,时不时浮于脑海表层,激起一波又一波水花,死死地抓着他的脑细胞,挤压着他的毛细血管,让他不能忘怀。他若不去,他原来的兄弟多少都能理解,也能谅解,可这些新来的,他们会怎么想,这头头
再忆起,还是伤出了老校门,穿过前面的马路,行到对面去,向左或向右走几步都会有一个小巷子,沿着进入,便到了人人口中的“罪恶一条街”了。那是一条不大的街,却云集了各式各样的小吃店、餐饮店,每天都会爆满的网吧,什么时候都不缺顾客的礼品店。礼品店是用来提供男女间互送的信物的宝库,小吃店里常迎来约会的情侣,网
爱,请深爱影与苗上次的长谈虽然是在图书室里较隐秘的地方,但诺大的图书室,总有人看到的。很快学校里就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议论着,但没有人敢在公共的地方议论,他们害怕其中有兄弟帮的成员,怕被打被修理。他们对于这两个人的相遇无比感叹。影是兄弟帮的帮主,是一个很强大的人,他们都对他惧而远之。苗是光电学院的
我要邂逅影在寝室里打游戏,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遂摘下耳机,起身拉开门闩。却看到小五布满汗珠的脸,便从手边拿来一块毛巾递给小五。小五擦去汗后兴奋的就要对老大报告今天的收获,影其实在小五进门的那瞬间就想问有什么消息的,却故作沉稳的说:“别急,慢慢说嘛!”小五放下毛巾欢喜的说:“大哥,那兄弟打听到了,那
初相遇遥望不远处,茂密的丛林为俊伟的南山增添丝丝绿意。丛林中冒出的小塔及几间庙宇为这座山营造了神秘色彩。山顶安置着的几条大广告牌,能见几个模糊的英文字静静地趴在那日晒雨淋的牌面上,没有几声抱怨。偶尔从山上飞下来几只欢快的小鸟,唧唧喳喳,像是在唱着什么祖传的歌,一只只亮起天使般动听的歌喉,没有哪只鸟对
宿舍楼与老校门两点间的水泥路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次下山、上山,吃饭、睡觉一遍遍的擦着路面覆盖别人的脚印,留下自己的痕迹从不愿在路上逗留,哪怕是短暂的问候熟悉的、半生不熟的人都是一个敷衍的照面,就是擦肩而过也是不愿的好友说我懒,不懂我的人觉着我冷漠其实,不是要紧的人不想多费气力不巴结他,也不得罪他着迷
我斜倚锈迹斑斑的围栏视线由近拉向了灰蒙蒙的天边那一瞬目光定格在城墙上的青石沿是久违的杨花飞我,想起了你某年某月某个黄昏白杨下踏着日落前洒下的余晖你我看那杨花飘飞秉着相机随着“嚓”的快门声起翩跹的你与舞动的杨花凝聚在一起这个星夜你悄悄的离去没留下一丝讯息我苦苦的寻觅徒增了数不清的华发郁积了鸣不出的伤悲
柔情的白月光倾泻到沙滩上,绵延的沙滩像水一样柔软,散发着微弱的光。海的广阔,视野里没有尽头,沙滩与海接壤,又增添了海的磅礴,让人没了希望,不敢幻想。如今,我面对这片禁海,面对着海里波涛汹涌的巨浪,一层一层席卷而来,它的声响就足以吞噬弱小的人,我只能暗自愁伤。我试图游过这片海域,走向这片海的中心,走近
我是一块石头。可能有些诡异,可我确实是一块石头。自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的体内镶嵌着一颗人的头颅。这颗头颅的存在使我拥有非凡的能力。我被安放在一间茅草房的木门一侧,这房里还住着一位忧伤的姑娘。我和这个姑娘相伴已有三年,不过,她不知道我的不平凡,她只知道我是一块石头,她倚靠的石头,她经过时纤手搭在的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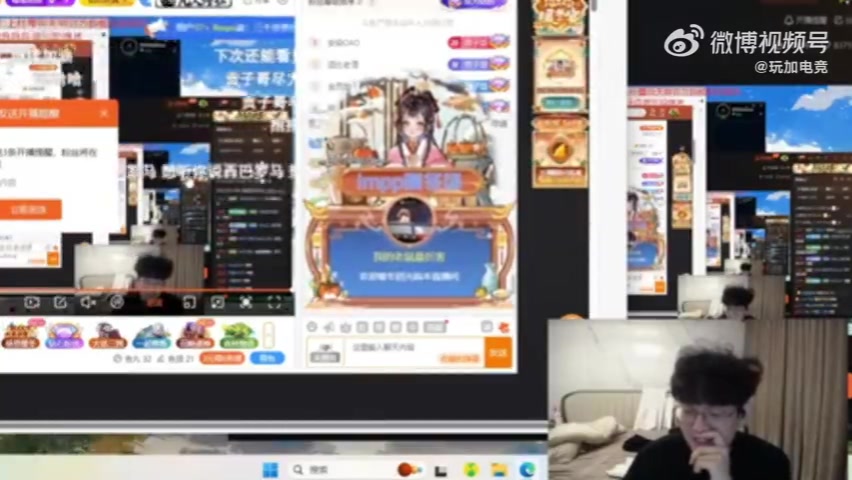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