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子死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虽然雁鬼说这早有预料,可我还是不能接受。我问雁鬼,此后还去不去绿霭山庄,他道,去啊,为什么不去,我还要去找我的老相好呢。雁鬼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只得向他点点头,你的老相好就是良子啊。他眨了下眼皮,道,你以为她的死能改变什么?我默然,想换个话题,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说的,于是我问他,你觉得良子是怎么死的。你真废话。他不耐烦道,自然是他杀。我再度盯着他,等待他下面的话。不
悬崖上的廊桥突然震动起来,他仍站在桥上不动,底下的河水流得很急,哗啦啦响着。他身着一件白底绣着黑色蟹爪兰的长袍,走到桥中心来,另一个他,穿着白衣黑裤,衣裳空荡荡地挂在他身上,他瘦,整个人像幽魂一样。跟我来吧,杀了他,你们都要偿命。穿长袍的人说。一个女子从后面走过来,她对着白衣人说话,白衣人没理她,由着长袍带他走了。一阵轻雾消失的声音。九和白衣杀了一个魔王一样的人,九不后悔,那个人早该被杀。但长袍抓
该是很久以前,那一天疏雨停歇,蜻蜓低飞奶奶们呼唤自己的小孙子爷爷卷起裤脚,把稻子中的稗子扔到路边那时候,土地里的土如此厚重你把它们挖来捏泥什么都不会,就捏了个棺材大人们火冒三丈你死活不改春夏交替,人们爱到井边洗衣洗菜绳子在轴轮上挣扎,一点点排好次序碱水煮了桂花叶绘好书签声音慢慢消逝了,孩子们不吃糖爷爷奶奶躺在黄土最后的棺材里是寂静的,地上和地下一样寂静蝉声作为背景,也一样躺进了装满土的棺材里黄土飞
我想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去看山春时树芽夏时蝉窸窣的声音让我觉得还身在人间秋时红叶冬来雪四季一眼明了自然贴近我们的胸膛又或是一叶舟,一片叶花期时一朵花的颜色细细,浅浅地抹在你小小的手腕上我恍惚觉得日子美妙
梦里有一场大雨的声音。清晨六点,你起床了,套上白色的立领裙,撑着那把颜色亮丽的雨伞,这里没有下水道,只有一条长长地裸露在外的沟渠,它被水灌满了,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切的景物都好清晰,远山依然朦胧,隔着不透明的雨幕。山桥快塌了,两头软塌塌地搭在两岸。地上是湿透的沙石,跑进鞋子里分外硌人。河边没有人,整天大河顿在那里,哗啦啦流水。烟囱不冒烟,没有蓝色的妖精染色青烟。湿润的味道横冲直撞,轻轻挽起你的衣
我们坐在同一辆列车上,他的管家拿着一枝红如鲜血的玫瑰,说它是栀子。我告诉他,那不是栀子,只是玫瑰。我家里种了一丛栀子,我从小看到大。他们相信了我。我们就此认识。他遇见很多女孩子,各种各样的。他开车来看我,同样被女孩们围住。他在包围圈里笑得很甜。你好,我是斯音。他来到我的店,一间在酒馆的包围中显得冷清的小店。你想要栀子吗,我问他。是的,我想把它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栀子并不廉价,特别是我的栀子。我知道你
佛,我已看透。他双手合十,淡淡地看着佛。我愿意放下所有身家,此生只愿跟随佛。贪嗔痴怒,你无一执着?千金绫罗,你只作云烟?人间情事,你毫无留恋?他再次看一眼佛。是的,佛,我已全部放下。佛轻轻摇头,目光含笑。看透不若参透,放下亦为拿起。虚无作有,有亦为无。你虽看透,却仍限于此,不能脱离。他笑。佛果然是佛,万年如一日,无怨哀,无悲喜。伴莲诵经……当真,不寂寞吗?佛没有回答。问他,大千繁繁,昌昌茂茂。你于
抬眼又闭张口无言今夜静在你的胸膛不动的流水躺在破败的河床你又想象墨被打翻黑色的舌头很快吞掉沾有昨夜残梦的字迹你在发呆又梦到谁对面楼在补眠守夜人的眼湮于暗里还有谁三更敲锣提醒你天干物燥灯与风斗舞交缠不休纵横着穿越每一栋楼希望你不要抬头看天空左不过几颗星星而已何必矫情卖弄你的伤春几斤几两众人都似明镜却如毒药越来越上瘾面无表情你从身旁走过我不知道你所愿是为何我知道你也不会说你紧紧闭着嘴拿起凉透的开水自己
《从前》多少年前的戏言在叫嚷着穿透时光闻一闻是否还有味道那段田埂的清香绿色纷纷扬扬被太阳晒得发亮我假想走过了大山挖走了月亮跟随灿烂的夕阳在忙碌的人们脚下蹦跳着拾着一根根麦穗拾到一个人的幻想水车被浸得发亮一片片升降舀起澄净的河水兜头浇在我身上我假想穿越了森林走遍了远方油菜和棉花深深扎根在土地上我随着它们一起长大将它们收获如果我当年种的那棵小麦它还能存活在美丽的秋天里它也会开花丰硕那不是戏言那是生命荣
从沧沥城到百伽关,中间隔了命运无法掌控的岁月。这么多年后,终是寻到了她,然而伊人现今如一盆即将燃尽的碳火,白发鬓角,容颜枯竭,这已如老人无异了。若一个人连心都老了的话,是任何药石也无法救治的。眠青的诅咒是一条长河,横亘了年少时深刻的爱恋,被提前的苍老打败。你打算怎么做?名水涟问道。苏恪脑海中依然有停不下来的震颤,此时竟无法开口回答。怎么做?进去告诉她,你就是苏恪?你找了她十年?此次回来准备与她相守
我的梧桐。秋天叶子落得很慢,春天生长非常快。此时绿色还很淡。会落很多年的叶子,也会冒着空气长出来。梧桐在想,曾有一个人在秋天走在它树下,只希望能有一片叶子落到她的肩上,后来冬天到了,她不再仰望他。梧桐在想,曾有只鸟停在它的树梢,只为给他讲旅途见闻南方的旭日温暖。然后拍拍翅膀,说,我要走了,你好好保重。梧桐想,曾有一阵风,在冬天寒冷的时候,携带碎雪穿过它光秃秃的枝桠,他们相遇只有一秒钟。这一秒中里,
昨晚我关掉灯,在梦中点上蜡烛然肉眼不比心神看不见你心我愿你的我的不只是人世间情爱两全还有自由功业需要你我成全同样是伶仃人生也无法重合相叠只让我为你点一盏灯在没有月亮的时候与黑夜道别火石蜡烛油灯钨丝打破时间限制就等在你的床边那都是我的意念从不让你探觉
整天待在家里,不与外界联系。当然不是世外桃源,那样我就扛着锄头了,过着什么心远地自偏啊,采菊东篱下的生活。或者是那个大学教书的美国女人,在乡下买一栋旧房子,种满橄榄葡萄香草,自制桃子酱,清晨边喝咖啡边看广场上农民卖西红柿。还有那个回归田园的摄影师,自己种菜种树,应季菜天天吃,爱收集捡来的碎瓷片,拍下年久被时代淘汰的物品工具。毕竟汝之牛肉,吾之青草,甲之熊掌,乙之砒霜。但,我也没有来笑有鸿儒,往来是
最开始在自己的思想与别人的目光里挣扎,每天针尖麦芒,郑重而可笑。生活始终是一个人的。外在的人只能于身外徘徊。与之相知,相伴,亦无法替代这副身心去承担苦痛流亡,这根线始终会断。孩提时代,与外界联系密切,吃饭,读书,上学,玩耍。密密切切造成生活实像。是你以为不可分割,不可离开。不可将生活揽到自己身上来,永远有人在你身后,收拾你的残局,摆好你下一次的位置。成年后或许明白,依赖不能长久。绕在周围密切的线,
〔梦谶〕蒸梦数十年,遗不过凡间。记忆无处索,不延年。抚碑于身前,自觉无惦念。繁数其种种,劫灰漫汝肩。经年明月,并合残缺。古道万里,海域艰。望不穿,天命所织的谶。困于哀石洞穴,乘彼毁垣,不敢动真言。怕所愿,如古物般湮灭。今生你煮沧海,我种桑田。睡在高山之巅,梦中再定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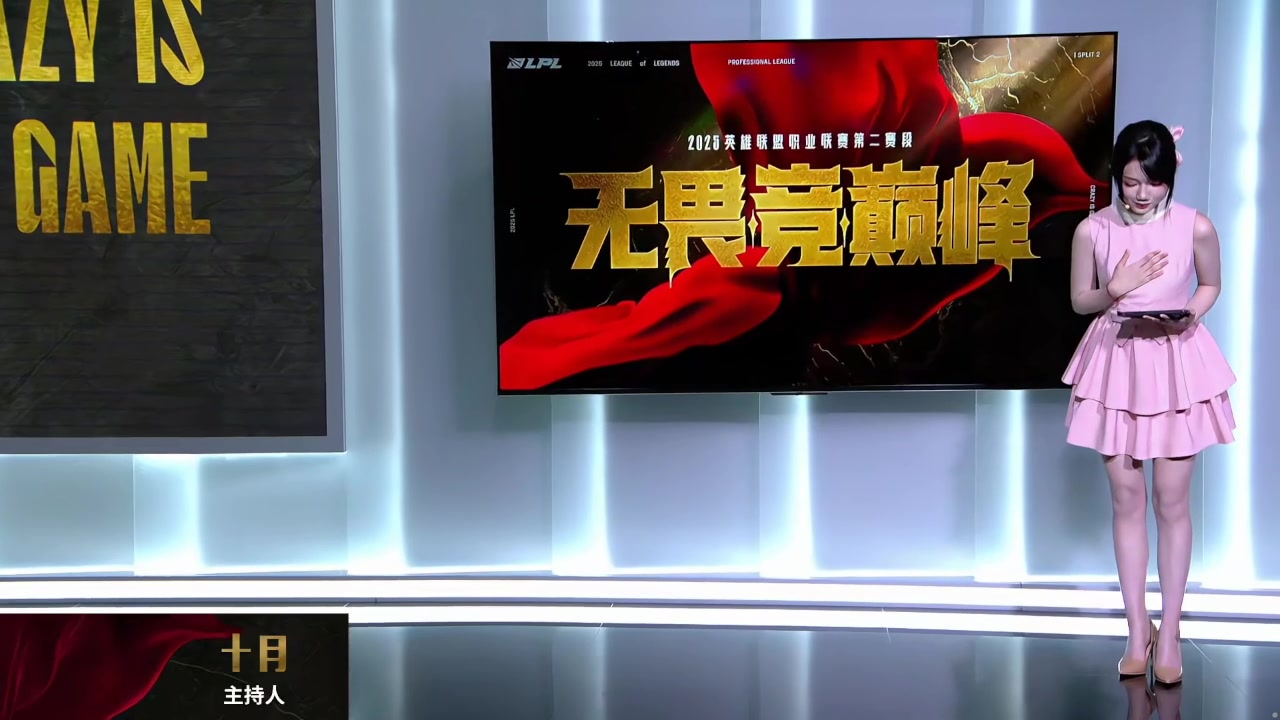 LPL互动主持十月身着粉色连衣短裙登场 修长美腿一览无遗
LPL互动主持十月身着粉色连衣短裙登场 修长美腿一览无遗
 京多安:曼城在二月份前犯了太多失误,俱乐部管理层需要好好分析
京多安:曼城在二月份前犯了太多失误,俱乐部管理层需要好好分析
 女主持人希然分享昨日工作照:月落星辉,这造型绝了~
女主持人希然分享昨日工作照:月落星辉,这造型绝了~
 阿斯:巴萨想签一名能够替代孔德的右后卫,多多和拉蒂乌进入候选
阿斯:巴萨想签一名能够替代孔德的右后卫,多多和拉蒂乌进入候选
 Angel发布上海烧鸟店探店Vlog:家世没网上传那么夸张 就普通家庭
Angel发布上海烧鸟店探店Vlog:家世没网上传那么夸张 就普通家庭
 今晚天王山之战!是BLG再取一胜,还是TES节奏控场更胜一筹?
今晚天王山之战!是BLG再取一胜,还是TES节奏控场更胜一筹?
 一老一少!森林狼发布赢球海报:康利和爱德华兹成为封面人物
一老一少!森林狼发布赢球海报:康利和爱德华兹成为封面人物
 解说王多多:赛恩最近很火,是不是应该多把巨魔拿出来呢?
解说王多多:赛恩最近很火,是不是应该多把巨魔拿出来呢?
 这么想打我?戈贝尔大帽老詹亮眼 贡献2分6篮板&正负值+14
这么想打我?戈贝尔大帽老詹亮眼 贡献2分6篮板&正负值+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