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着未知的夜空,聆听着嘈杂的蝉鸣,我的鼻子不禁一酸,温热的液体顺势流下。外婆和妈妈到达广西了吗?外婆的病可以治好吗?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孤独?当我听到外婆摔断腿消息的那一刻,我的心泉俨然变成一潭死水,我像疯了一般只管拼命狂奔,冲向地里的妈妈,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把妈妈叫回来。最后,大家做了决定,舅舅和妈妈带外婆去广西做手术。我用指甲狠狠地掐入自己的肉,阵阵痛意袭来,我才如梦初醒,接受这个事实。妈
我八九岁时,出到了河坡。这里爸爸种了好大一片果园,全是马水桔,绿油油的叶子,编织成一块大绿毯,万绿丛中一点红,这点红便是新起的红砖屋-我们的新房子:红彤彤的四周和顶端黑压压的瓦片的巧妙组合就是我的第二个家。那宛如黄泥般的记忆随着北风的脚步走了,崭新的世界向我招手。土地再也不是乌黑泥泞,取而代之的是软绵绵的似海绵的细沙,光着脚踩上去,又软又暖,比踩棉花还舒坦,那可真叫一个享受。新家周围还有不少惊喜呢
“你......你外婆昨天走了。”电话里传来妈妈沉重的声音,每一个字好比一块巨大的石头狠狠地压在我心头,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无法想像,我心中那个最可爱的人已化作一抔黄土-永远离开地了我,而自己却无法再见她一面。记起最后几次探望她时,身子弯得如百年老槐,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如干枯的松树皮,似脱过水了,风抚摸着如雪般的银发,嘴角露出如春光的笑容。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外婆,但那个美丽的笑容却肯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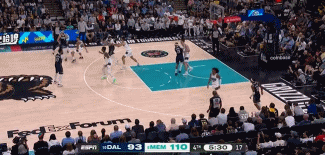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