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是九月的最后一口酒。在眩晕了30秒后,醉倒在枫叶的情丝里。十月是岁首抛出的第一个绣球。只为恋着白雪的风韵,而迟迟不肯落下。十月埋首于秋的臂弯,腮红是迷人的诗篇。落花起处,有女儿红的醇香。十月咀嚼着日子的贪婪,清泪忽而如线。秋千枯萎了裙裾,每一声叹息都恍如百年。回首走过的沙滩,十个清晰的脚印已被风
你明亮的眼睛原本盛满了阳光是什么使它如此哀伤灰色的空气里眼泪疼得看不清方向你天真的眼睛从未有过沧桑是什么使它如此迷茫喧嚣的大雨里再也找不到爸爸妈妈的臂膀当风吹皱了你稚嫩的脸颊当你见人就叫“爸”、“妈”天空哭了满腔的怜爱在脚下的废墟里安家大地哭了开裂的嘴角边噙着黄连雕刻的花山哭了水哭了漫山遍野的帐篷哭
手拿遥控器,坐在电视屏幕前,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透过电视画面,我看到了大片大片的瓦砾废墟,看到了号哭抽搐的人群,看到了如猛兽般张开血盆大口的地面,还有那昔日的高楼如今成了支离破碎的九节鞭。硝烟四起处,我仿佛听见了人们或断断续续或高亢急促的呼救声!──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有些无力承受,不忍
夜深了象朦胧的粘贴画早春的蝉蜕伏在摇曳的枝头二月二的鞭炮声倏忽变得那么遥远满地缤纷的落红一跃而上谁家的窗站在梦的尽头看见自己曾如黄花般消瘦一声呓语打碎了三更的夜漏月色如霜照着一个孤单的风筝那是少不更事的风风筝唱着风却在哭泪滴在回忆的掌心压缩成一个薄薄的影子
从前是一枚邮票站在信封的高度浏览全球的邮箱现在是一个信息和着彼此的呼吸走在网络空间里夜深了金黄的月晕滑着狐步一个华丽的转身天空的脚面上留下一张黑白的底片和岁月无声
雪快化尽了冻僵的地平线找回了呼吸打个响指乘坐最古老的雪橇狗儿象天使咻咻的气息里拌着蜜一部长长的白胡子不时挡住它们的视线于是只好暂停一个叫圣诞的东东趁机抢走了它们的行李一路哈哈笑着走进最近和最远的星星树里
今天天很好淡淡的日子在淡淡的目光里开花今天风很轻悄悄的话儿在悄悄的恬梦里发芽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那承载了一辈子光阴的骆驼是的我想叫她骆驼因为她宽广的背带我走过生命的沙漠是的我想叫她骆驼因为她不知疲倦的脚掌积存了那么深的爱的源泉她也有白发了藏在驼峰深处的记忆在皑皑的雪里掩埋她的脾气越来越温和了只那斑
春晓的声音象风拂过堤岸月儿弯弯曲曲象路横亘心间三条河流生生不息在掌心打一把共同的伞叶子绿了的时候鸟儿粉红的喙是最醒目的樱桃簸箕和“斗”是雨后的蘑菇年轮住在光滑的纹理间一个经年的伤口裹着沙石的微子将生命线分作两个遥遥相望的渡口
淡淡的花香在口边徘徊轻灵的羽毛在梦里盛开骤然醒来披一袭朦胧的思绪阳光化作佛手抚灯座上的尘埃门铃醒着明亮的瞳里写着时间耳朵上别两朵深秋的菊我知道了那花香的源头
梦的尽头是清醒就象夜的尽头是黎明心的尽头是真爱就象目光的尽头是迷宫路的尽头是远山就象时间的尽头是无穷世纪尽头是一个未抽丝的茧是一把缠满问号的线轴尽头的尽头是欲语还休
如果你以为甜儿是一个女孩的名字,那你错了。甜儿是我家的甘蔗。我是伴着甜儿长大的。那时候,我家有两个园子,一个种菜一个种高大的植物如向日葵还有甜儿。甜儿是瘦削的,精灵一样,风过处,轻轻扭着颈子,一袭淡绿的纱衫在夏日里格外动人。它有些竹的风韵,也是一节一节的,远看颇似丐帮的信物——绿玉竹杖。每逢甜儿快成
小时候,爱看各种各样的书。金庸古龙漫画迷宫诗歌小说散文传记都是我涉猎的对象。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幸福”这样的字眼儿。最初并不理解“幸福”的含义。心想,象我这样,安静地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披着阳光懒懒地翻着书,就叫幸福了么?稍大些,到姥姥家过暑假。常跟小姨一起去南沟西沟放牛牧马采花摘果,日子过得
我小时候,极爱吃杏儿。我家没有杏树,姥姥家有。于是,每年暑假,我都会徘徊于她家果树园里,不吃得牙酸齿软,绝不罢休!有时候,还没到果木成熟的季节,青里泛红的小杏儿对我来说,竟是绝好的美食。哈,物以稀为贵嘛。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新分来几个实习老师。有个女老师叫婧,皮肤白,体态丰腴,声音清脆得象银铃。她教
今天是8月23日了,想想看,快到爸爸的生日了。给老头买点什么好呢?我爸爸真的是个老头了。胡子拉碴的,头顶上已是花白一片。60岁的他身姿依旧挺拔,却不可避免地现出了老态。眼角的皱纹很多了,嘴角一咧,面部肌肉也明显松弛了好多。呵,那个腮帮子青幽幽的爸爸呢?那个头发粗粗黑黑手脚麻利有力的爸爸到哪里去了呢?
在岁月的河流里,我是一只无尾的鱼。那尾巴恋着13年前的呼吸。我不想拿回它,宁愿在疲惫了伤心了惆怅了开心了忧郁了的时候,回望一眼,只一眼,就足够了。13年前,我在旗中学念初三。班里有50多人吧,后来同届的5班解体,又流入我们班20多人。这样,统共有70余人,也算泱泱大班啦。班主任姓焦,圆脸,烫发,兼任
儿子长得真快,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很多衣服都穿不了了。偶尔把它们拿出来,搁在床上,一字排开。看着,就莫名地湿了眼。那群小东西精巧得象十字绣。时光的针嵌在上面,只余闪亮的一点。跟儿子一样,我的小衣服小帽子也被妈妈压在箱子底儿。我出生后的第一件衣服是暗红色的,布料很粗糙,做工也不那么高明,倒象有年头的
我叫她四娘。确切地说,她是我老公的四娘。她是个典型的农村老太。个儿不高,体胖,头发光溜溜梳在脑后,一丝不乱。鸭蛋脸上,眼袋略大,眼泡儿有些肿。眉眼几乎总在笑着,干练里透着慈祥。她有仨姑娘俩儿子,都成家了,只剩她跟四大爷老两口独自住在一个干净的小院里。四大爷很高很瘦,身板很直。性子也正直,只是有些不温
上幼儿班之前,我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那时候,我叫“王素燕”,是燕子的燕。也许爸爸的本意是要我象燕子一样朴实勤劳吧?可我对于这名字极不满意,因为它不够悦耳动听,还与老家一小我好多的堂妹重复!可我有啥办法呢?户口本上落的就是这么个俗名儿。曾翻过多少遍字典,想为自己更名,却无功而返。有些字好听,但字太生
某个周六,我休息。儿子却不让我喘息片刻,直嚷着要出去“溜溜儿”。无奈,妥协了。想想门前正在修路,就不去广场了吧。索性打车前往中心街。5分钟后,熙熙攘攘的人群伴着鼎沸的人声出现在眼前。猛醒,那日竟是大集。库伦的大集每月两次,分别是初一和十五。于是每个月我都要犯愁两天,人太多了。骑摩托车太费劲了,跟蜗牛
已经有十年没吃过西部区的酿皮了吧?时间过得可真快。有时,望着镜子里那个日渐丰腴的自己,甚至有些陌生。中专毕业时还那般纤细的女子到哪里去了?那个爱吃巴盟酿皮爱吃炒饼焖面却咋吃也不胖从而羡煞众人的姑娘到哪里去了呢?无从找寻。除却落满灰尘的纪念册。可是,相册里却是任你咋闻也嗅不出那迷死人的巴盟酿皮的香味来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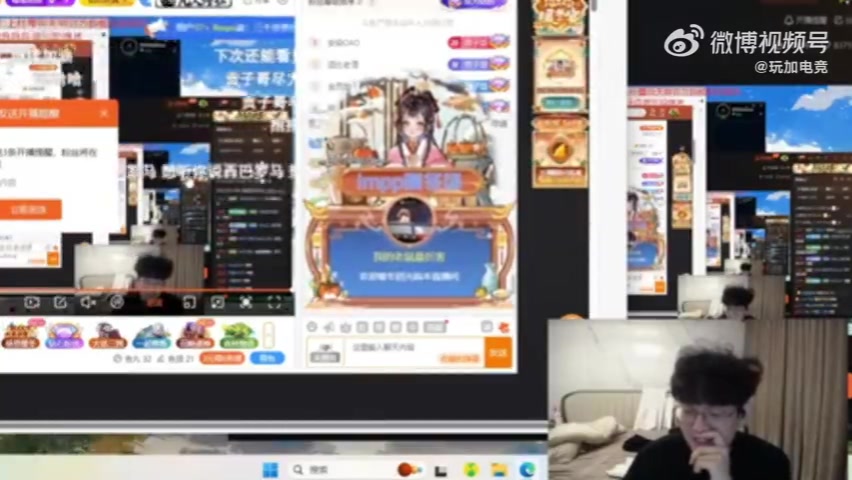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