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群里,看见你木然的背影幼时的爱恋如揣了心事早凋的石榴只留给自己一坨坚硬的疏离时光温柔却也化不开滞留在无奈里的忘却我说走过去忘记转身处,谁昏黄了我一眼的旧事温柔
上个星期天正在睡觉,六点多妈妈打来电话,那熟悉的声音里浸透了疲倦。我很无措,突然觉得面对她无来由的悲伤,自己多么的无能为力……沉默了很久,她才幽幽的说:“婷儿,如果有一天你得了什么病,不要一个人撑着,记得告诉妈妈,妈妈养你这么大,真的不能在不知晓的时候失去你,你不能自私,不能……”我突然觉得很悲凉,
屋檐绣了青苔瓦沟里倒伏着陈年的植物带着腐叶味道的滴露从瓦缝流了下来我侧耳听石磨伴着外婆拉千层底的声音琐碎的走着磨眼里流动着黄灿灿的玉米我仿佛看见黄昏时灶台旁饥饿的眼睛松明子的香游走在老屋的每一个旮旯粗瓷碗暗淡的呻吟控诉贫穷和那些在贫穷中淡然的人们但我渴望那种饥饿让我记起《吃土豆的人》那些木然却又淡然
母亲:您好!很想念您叫我小名的那些日子,即使不温柔,我也一样觉得幸福。您在外漂泊已数十载,我不知道孩子在哪一次的不小心中中伤了您叫我小名的习惯。记得小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河边留恋忘返。看那些才长出绒毛的小鸭子戏水,听风吹过竹林时沙沙的竹涛,眯了眼看夕阳西下时淡淡的晕,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回家,我不知
铜锈惹了门环芭蕉惹了夜雨谁打江南走过惹了一帘思绪清梦一场都市的寂寥启不开清瘦容颜下遗落在江南乡村的绮丽拾起往事里的羽衣淡泊一地孤寂
唐代的雍容凝重在散着墨香的文字里呻吟一个时代的沉香只配画今日篇章中背景的苍凉千万的重量生硬的涉入现代文化的荒凉浮华的句读如何半掩文学致命的虚肿我们仅窃了古韵的躯却把千年的书香、陈迹遗落于梦回荷仍香的古时谁又是古韵的产婆沾了的血污只是古韵书香的胎衣婴儿早已窒息、死亡
行者夜语题记:污浊的火车厢内一片狼籍,我的眼辗转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或村庄,放肆的泪落了下来,为那些与孤独有关或无关的候鸟和炊烟,及那些成熟而凄美的心情。有狗尾巴草的梦白天,我沉睡,拒绝阳光下破旧而艳俗的景,在车厢混沌而又沉闷的气息中,以梦掩饰行者对昼的无奈。火车咔嚓咔嚓的切断了一个又一个燃着九月
外婆家的小院被一圈石头围着,青黑色的石头上有淡白色的鸟粪和村童用炭画下的门神,用手拂上去,是一种粗糙而简单的脏,一眼便可窥见石头安静、温厚的心。院内有栗子树,瘦小而又坚挺,很倔强的样子。树上常是挂满了棉布袜、破布片和干辣椒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树拒绝结果实。冬天落雪的早晨,一大群鸡在树下、檐下徘徊,
一池思绪该以雨天做注脚罢淡淡的湿气弄潮了干燥的心情北方汉子黄土般粗犷的秦腔也捂不干湿润的叹息滴水的思量加了梅雨的绵长浸透山南水北的遗忘午夜梦醒蹄声四起打翻一池的期冀
数次提笔,却终是莫名的空茫,心中有许多感觉,找不到一个词,能够抓住那些冬日落雪夜晚的空灵,形容词和心绪的角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公平的。我只能忘却它们的滞后,在我尚有勇气写的日子记下我这已亡的22年,聊以祭奠我曾经不甘平庸的挣扎。(一)、懂事以后当我在赎罪的重压下活得太累时,总忍不住自问:有些人来到
相识原来如此简单如同挥手拂去阳光落在我鬓角的余温忘却竟然这般难咽恰如伸手躲避夕阳的伤感它却又在下一个午后把微薄的已愈的伤痕划拉开一条长长的带温度的伤口
父亲,我知道您在叶子烟、二锅头中已沾染了太多的淳朴和世俗,显然那些散着书卷气的谢谢远离了您的生活品味。因了任性和掩饰,我在陌生人跟前自然出口的谢谢于您却是如锈了的镰刀刃,听来是那般的生涩和别扭。只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寻到另一种倾述我万分之一感动的方式,一种我可以支付并且真挚到不带一丝应付色
一池漂泊思念是池中萍春夏,东西的变更因了地域的相阻欲厚还薄只是萍上始终有一条叶脉纵然是山南水北,纵然是绿了芭蕉瘦了古道它依旧如蛇行的小径在叶柄处凝成一个不盲,不锈的斑痕漂泊的人儿笑一声,哭一声叶脉就扭曲不堪,即使用了千年陈酒也浇不平屋顶的笛声一抖思念便如揉碎了的多汁的叶流了一手的是深秋时节子夜的寒露
外婆家的小院被一圈石头围着,青黑色的石头上有淡白色的鸟粪和村童用炭画下的门神,用手拂上去,是一种粗糙而简单的脏,一眼便可窥见石头安静、温厚的心。院内有栗子树,瘦小而又坚挺,很倔强的样子。树上常是挂满了棉布袜、破布片和干辣椒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树拒绝结果实。冬天落雪的早晨,一大群鸡在树下、檐下徘徊,
(一)、每年种麦的秋、冬之交,黄、白的菊花就漫山遍野的迎风自醉。田垄边、山脚下、荒地畔,浓烈而又热闹,一簇一簇,一片一片,灿烂到恰似烟花在空中的绚烂一样味道的寂寞,喧闹至忘却了时间与阡陌的荒芜,没有人管,它们便由着性子的开,似乎不知秋是个头儿,还是冬是个头儿。苦而浓的香让鼻子有种感冒时的不畅,然而胸
把那些眷念与遗忘揉进睡与醒的夹层梦里梦外都是斑驳的感情而我们却麻木的忘记了周遭的纷杂纵是身逢绝境却装作在心中觅不到现实的刀光剑影原来沉沦可以隔绝心与俗尘......
拂了又来那些日子的脏黏在我薄薄的记忆里如蜻蜓的一只薄翼撕破了经纬却再也无法将那些生之净中暗涌的污拨去一个人走路连双脚划出的线也是空洞的我再也无法以闭眼说一个忘却的借口那种薄凉的执著让我有种生的苍凉脏乱的清醒中请以我已厌倦的俗的身躯作一方棺衣掩却圣水难去的耻与无垠的恶
擂,擂一江男子豪情锤,锤一池慈者清泪荡开的,是血是肉腾起的,是情是泪鼓起三更鼓断黎明高粱酒的霸气肃杀了耕者的艰辛艾草的清苦滋润了土地之子心口的寂寥一山鼓音的长嚎里有谁带叶子烟的啜泣是生是怨还是无由的承诺压一身重债在地垄给儿翻耕荒芜的希冀
陈诚,男,武汉某大学后门卖凉面的小摊主。陈诚当年考取武汉的一所大学差三分,任他娘剁烂了砧板咒他不争气、该死,他只是低了头淡淡的道:“俺不读了,俺想在那学校后门摆个凉面摊去。”他娘一扭屁股,嘭的一声甩上门,被风撞进门里的是:“你个背时不长良心的东西,看你卖凉面能走出这土旮旯去……”其实陈诚本就未想过要
一片青瓦,一眼古井,一领破席最初的梦想恰如一粒豆儿瓦上的苔痕,井沿上的屐印,席缝里的汗味,染了些她见风便猛长时光荏苒最初的梦被现实咯痛隐隐的,是种无奈故乡落雨的夜瓦亮了,井满了,席潮了勾起些琐碎的思念最初的执著如潮水来袭打开窗,清风洗面风,恰如当年豆儿发芽的那个清晨
 纪录片《眼见为实》 圣枪哥一步之遥的遗憾
纪录片《眼见为实》 圣枪哥一步之遥的遗憾
 前LPL英文解说Kitty晒上海Major现场照:被导播拍到啦!!!
前LPL英文解说Kitty晒上海Major现场照:被导播拍到啦!!!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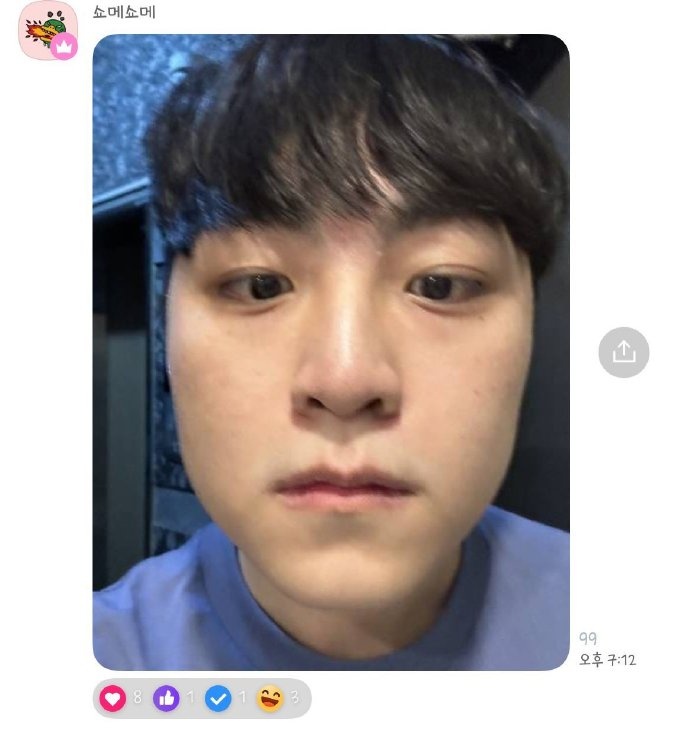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