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在歇马亭村一抹光亮 ---记区自然资源局派驻歇马亭村第一书记刘学亮 “你要往哪里走,把我灵魂也带走 .....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华
在余光中老先生记忆中,小时候的乡愁是一枚邮票,他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我,乡愁是老家院子里那棵红枣树,我在城里,它在老家……七、八岁时,父亲从外面移来一棵小枣树,有拇指一般粗,栽在了老家的前院里。父亲说这是棵脆枣树,叫六月鲜。这显然是听枣树的原主人介绍的。以前的乡下,大多数人家都喜欢在院子里种棵枣树,一是红枣晒干能冲饥,二是喜欢枣树“早生贵子”的谐言之意,吉利。再就是,枣木瓷实,木质硬,打家倶
走过那条僻街的巷口,远远地又闻到楝花香。那是一种十分浓郁的香,浓浓的香气中带有一丝丝甘甜,钻进喉咙,直入肺腑。偏巷里那株楝花开了!我不由信步向里走去。春夏之交,是楝花开放的时节。他们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隐藏在细碎的绿叶间,远远看去,就像掩映在绿叶间片片温柔的云朵,一片氤氲。微吹来,阵阵清香随风四溢。我走近那株楝树,花期正盛。鲜嫩的枝叶间一簇簇或暗红、或浅紫,或兰白相间的楝花在明亮的阳光下舒展着
老家门前的大路对面是新修浚的凤凰湖,风光好,视野也很好。冬春季节,晴朗的天气里,红红的日头上到三竿高,阳光开始照到我家院子南墙上,一片金黄,暖意洋洋。随着气温的升高,走出家门的老人们踽踽而行,有的从大街的东头走到大街的西头;有的从大街的西头走到大街的东头,然后拐到我家大门外。有的则直接走到我家大门前,围着凤凰湖转上两圈,看看湖里尚未干枯的水草和偶尔起飞的山鸡水鸭,听听周遭树枝上或塔松间鸟雀的鸣啾欢
江南好,风景旧曾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下江南,孩童时期便是我最神往的一件事。父亲在的时候,他朋友多。一些走过南闯过北的客人在酒桌上吹嘘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时候,心中的江南除了美景,便是家家户户都过着酒盏交错、鱼肉飘香的富足日子。后来,说书的老瞎子,隔上年把半年便落脚到我们队的牲口屋。天一晚,全队老老少少就陆续围聚在充满捞草缸味的牲口屋,听些才子佳人、王侯将相的传奇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今年立春早,南风勤,春节第一天,就感受到春的讯息。大年初几,一个暖阳融融的下午,陪着孙子到护城河散步。河畔一簇簇、一片片焦黄的迎春花,老远就映入眼帘。那娇艳动人的小黄花,让人无名中产生一种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萌动。虽然,一阵阵的河风吹到脸颊上,还有些微凉。但这是春天的风。迎春花一开,气温就悄悄地升高了。我对孙子说,春天属于生机勃勃的季节,对于人生来说,青少年就相当于春天。
天晴了,路旁银杏、法桐、白腊等树上的树叶在明亮的阳光下由绿变黄。两场秋雨二十多天,硬生生地把季节从入秋拉到晚秋。冷风飘过,黄黄的树叶便有一些随了风向,在空中飘舞,而后追逐着向远方洒落而去。地上很快就积起厚厚的“黄金片”,随车辆、行人不断地荡动。附近的灌木丛中,红叶女贞和结果海棠,经过寒露的浆洗,早早把红色的容颜展示出来,为萧瑟的墙角增加了色彩和情调。各种缺乏勇气跨越寒冬的花卉及作物,无不紧紧抓住所
小屁孩,一般称呼有点淘气的小孩也。小屁孩是他娘三十九岁生下的。这一年屁孩娘三十九岁,屁孩爹四十二岁。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生活的村庄是很少见的事情了。这有当时流传的一句口头语为证:“女人三十九,亲戚关门走”。也就是说妇女到了三十八九的时候,“身上”就没有了,“身上”没有了,自然也就没有了生育能力。小屁孩的娘生下屁孩的时候,年龄偏大,也成了男爷们粗野的谈资和婆娘们私语的话题。议论归议论,屁孩爹娘
凭轩望秋雨。秋雨绵绵,浸润着墙角路基,我不禁挂念着老家的老宅。老家距县城四十华里,居镇上十几华里。村庄大不,但历史悠久,人烟繁旺,几个自然村接连在一起,颇有村镇的气势。前几年搞合村并居,几个村庄建一个新的标准化社区。我的老家也在搬迁规划之列。看着邻村拆迁工作搞的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一段段往事湮灭在尘土里,一片片老墙旧瓦复垦在庄稼下。老家就要拆迁了,老屋也即将不复存在,心里难免涌出一丝丝的婉惜。这种
随区里组织的乡村记忆采访组采访,乡间里那些被冷落了许久,甚至快要被忘却了的记忆,便又被提了起来,串起了一个个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的话题……然而也有一些,是让我感动,永远都不能忘怀的精典故事,那是红色的记忆……红色记忆之一王伟登高一呼,成立“抗日独立连”王伟原名张学虔,1910年出生,兖州西北部三十里河南村人。王伟自幼习武,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也练出了一身好武艺。1932年,参加省主席韩复榘主持的全省
(一)求雨一百年前,中国尚处在靠天吃饭的农耕年代。那时候,农民没有现代意识,没有科学观念,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以外有一种超现实、超自然的力量。于是,在人们遇到现实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就去寻找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又企图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利用他。这就产生了现代人看来近乎荒诞和迷信的巫术,比如求雨。在华夏大地,每村都有求雨的故事。我的家乡位于黄淮平原的主要粮食产区,对雨水的依赖尤为重要,旱季求雨自然成
一挨秋风乍起,出伏的蛐蛐们便耐不住寂寞,田野里,小小精灵们就会鼓动声门,发出让捕捉手充满激动和欢快的大音。兖州北部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上盛产优质蛐蛐,玩家门称其为“秋虫”。古时,这里的秋虫曾是王公贵族们的玩物,当地百姓上缴的贡品。立秋以后,京津浙沪等地的蛐蛐商人便趋之若鹜前来淘金,争相选购“好秋虫”。每年一靠近立秋季节,各个村子里就三五成群住满了操着天南地北口音,大腹便便并且腰带上总是系着一两个鼓鼓
夜漆黑,街漆黑。街两侧的树木,在夜色的笼罩下,更是一片片、一团团的黑中之黑。临近严冬的夜晚,在镇街上游走,倍感寂静与清冷。树是塔松、女贞、法桐等常青树或冬季落叶较迟的树木。树木整齐划一的排列,密密匝匝的枝叶,无拘无束的长势,使这静静的夜晚又有了些安详与神秘。“扑楞楞、扑楞楞”,忽然从哪棵树木的枝丫间传来了或许是夜鸟脚下不稳,或许是打盹打得猛一些机灵而挪动腿脚忽闪翅膀的声音。幸亏种了这么多树,我心里
卧室的窗正对着一条街。透过玻璃窗,街两侧整齐的法桐树便展现在眼前。一日,站地窗前望景,猛然发现,窗前这棵桐树与他的大多数同伴还是很有些不同的。虽然已是深冬,大多数桐树的叶子都已落光,只剩光秃秃的枝条。在空中支架着,象老年人的筋骨。而窗前这棵,却很是有些风姿,仍然挂满了树叶。黄黄的叶子晃晃悠悠,象随风摇动的旗子。而枝叶间一串串的桐球,则象喜庆的小灯笼,一颗颗、一盏盏、一串串。看上去树叶甚至已经干透,
蝉鸣半夏生。夏至过去一周,耳畔还没有听到蝉鸣。坐在书桌前,翻几页书,呆望片刻窗外的柳枝,心中有些落寞。没有听到蝉鸣,就是蝉变少,自然是爬出地面的知了龟数量少,成不气候。对我来讲,随之减少的不仅是夏天的物化特征,更是时光的流失和心底的记忆。可能是渐渐步入老年,近年来,儿时的记忆开始常浮上心头。小时候的世界单纯,大多记忆是伴随着吃而深刻的。对夏至节气记忆深刻,大约是可以捉知了龟了。“夏至二候蝉始鸣”,
过麦刘长秋文“麦儿黄,麦儿黄,过了端午吃新粮。”农历五月,是黄淮平原收麦的季节,俗称“过麦”。有句农谚:“一麦赶三秋”。这话什么意思呢?“一麦”是指麦季里就一个活,收麦子,把麦子颗粒归仓才算大功告成。“三秋”是指秋收、秋耕、秋种三项活。一麦赶三秋就是说麦季里活急,活累,堪比秋收、秋耕和秋种三个活加一快。麦收有多急呢?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早晨看着麦穗麦秸还泛青,经过一晌毒毒的日头暴晒,加
邻居大哥是党员--我的入党故事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生活虽然清苦,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好,政治觉悟高,信仰坚定。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邻居大哥是一名党员。大哥虽然与我同辈,但是年龄比我父亲还长一两岁。大哥参加过解放战争,负过伤。最初,大哥是当的国民党的兵。因为家里穷,吃不上饭,就跑出去当兵了,就是俗话说的当兵吃粮。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虽然也训练军事技术,也有严格要求,但是当兵的都没有信仰
我的老家离县城比较远。从参军离乡,到从部队复员落户县城,就很少回老家居住。自从父母老去,每年回老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次清明祭祖回老家,到老院转了转。老院的院墙残缺不全,残存处不足一人高,院子空地被邻居开垦成菜园。老屋外墙抹的石灰皮多处脱落,露出土坯垒成的底子。唯有那棵老槐树依旧傲然倔立,枝头隐隐抽出嫩嫩的细芽。这是养育了我们姊妹六个的老院,承载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老屋盖于一九六四年,那年我虚岁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外孙正朗读着课文,忽然放下课本问:“姥爷,书上说床前明月光的“床”是指水井围栏?水井是什么样的?”水井的样子,现代的小孩大概只能从书本或影视作品中去寻找了,而对于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祖辈们,一口老井则是家乡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小时候,老家南园附近有一口老井,我爷爷说,是他爷爷的爷爷淘下的。这口老井是我们刘氏家族七八代人赖以生存的
幸福可远不可近——小老百姓的幸福是指点江山、不议论身边因拆迁,我暂租居到北关新村。北关新村地处主城区边缘,一个大型国企与两座铁立交桥围成了一处“世外桃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关村迁居人口渐多,就在这里划了一个居民区,所以叫北关新村。新村的周边呈扁圆形,二百来户人家大部分是铁路及旁边国企建设时依村落户迁入的人口。年青人都如羽翼长成的鹰,飞出新村、落户到外地或主城高楼大厦的新小区里。留居的,大都是六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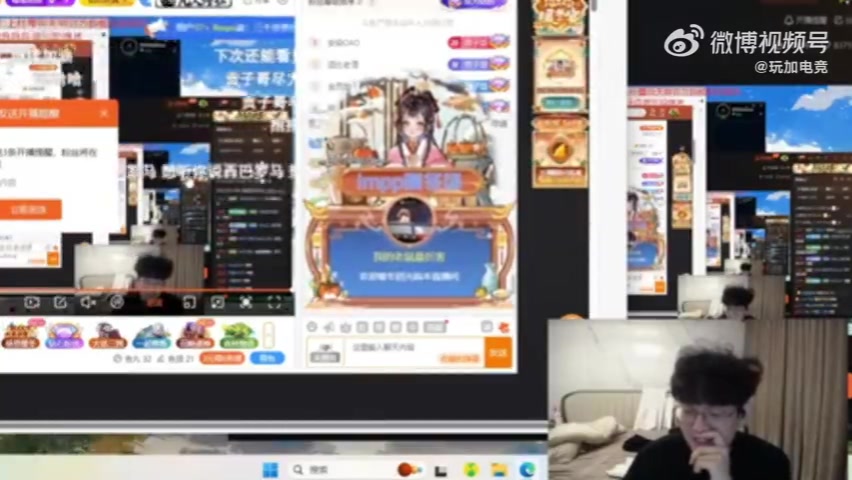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