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望到走近,从走近到接触,从接触到投入哲学,这一路我化了几年的功夫,到得现在,我揭开了哲学那层面纱了么?我想,并没有的,我不过透过这薄薄的纱巾,看到了些若隐若显的东西。要真正走进哲学,那会是一条需要用一生去走的路,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追随的理想,是一本即便用去一生的时间也读不完的书。我想,它永远会在
哲学,它永远对我保持着它所应有的神秘,我却总想揭开它的面纱。在不知多久以前的以前,当哲学这个词最早进入到我的脑中起,它在我的想象里就一直都是个神奥的东西;即便到了现在,哲学在我的眼前也仍然披着层神秘的纱巾。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有一个教哲学的教授把第一堂课跟最后一堂课的主题都设定为“哲学是什么”,而
开头起先,还是要来说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所谓的“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个很“初始”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很“终极”的问题。说它“初始”,是因为一般要去研究的人,第一个就会遇到它,而且避不过,倘使对它没有一个自己心里清楚的解答,那应该就算未入门了。而说它“终极”,是因为研究到最后,你所要面临的仍然是它
路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一般在先都会预设一个目的地,但只为了走路而走路的人也是有的。不过即便有了目的地,却未必知道方向,未必知道怎样走下去;路总是要一步步的走下去的,走着走着,渐渐的你会发现其实这就是你所要走的方向,你目的地就在前面。但或许你终于会发现,这不是你应该走的发现,这样的再走下去,你到
最近总写不出东西来,而久不写文字的那种“负罪感”也几乎消淡了,没有人催逼,自己也不催逼,有时候真想就这样沉落下去。这就像久困的人,象心纵意的躺倒在床铺上,闭起了眼睛,就再也不要睁开来。然而,时间久了,终于还是会醒来,我们就都是这样,苦于不能一直的沉睡下去。而当这偶一时的醒着的时候,我又想找来找去的找
写到这里,终于是到了最后一篇,一件事情有即将宣告完结,我几乎又可以“叹一口气”了。为什么是“叹一口气”呢?是我常把叹气当做深呼吸的,其实,动作都一样,也是先倒吸一口长气,然后吐出来,只是心境略有不同罢了。本来,一篇甚至一个“系列”的东西写完,是应该“舒一口气”的,但我每对于所写出来的东西颇有不满,而
这一个系列写到这里,竟然写不下去了。这倒不是因为涅槃这“无境之境”本来是“不可思议”的,而是我自己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不想说,至少,我不想在这里说。总之就是,心里浮躁得可以,年岁愈增,却发现自己愈不能控制自己了。到这时,我也实在开始有些佩服这些佛门弟子起来,能守住自己的无量欲望。在我,是做不到的
一切机缘成熟,理所当然的,释迦牟尼佛开始了他的理想的第二步——度化众生。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这也是一条可以让人感得绝望的道路。这样的理想,注定就只在于理想之中,是一个达不到的境地;对于这样的理想,你所有的只能是一个“希望”,一个来对抗你的绝望的希望。大多数的时候,相对于念想中的“受众”,所谓的“
但凡伟大人物的理想,并不是只到了自己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就算完的;但凡称得上伟大的理想,都是跟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其实,悉达多或者别的什么伟人们,他们自己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或得到“至高真理”,这些,只不过是第一步——使自己有了可以说话、可以让社会有些改变的能力或者地位、有了可以把理想坚持下去的
看来,这株尼连禅河旁边、伽阇山山麓的毕钵罗树是不平凡的,它注定要跟悉达多太子一道,成就无上正果。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话虽不好听,理却是这个理。悉达多在这株毕钵罗树下,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果位,获无上正等正觉,成为至圣佛陀,为三界独尊之天人师。而这株毕钵罗树,也就此被封为圣树。据《大唐西
当悉达多太子觉到现世的大苦楚,也约略看到心中的理想之境,进而生出出家修行之意时,他遇到了最严重的阻扰。这阻扰比任何修行中的挫折、任何身体上的苦痛,甚至比“日食一麻一米”而饿得“身如枯木”,还要严重得多得多。这阻扰就是来自于悉达多的家人们。那位对他几乎倾注全部的爱与希望的慈父,其时年事已高,悉达多的贸
人都是趋乐避苦的。不单是人,一切的有情众生,也都是趋乐避苦的。当人在看到、甚至体味到现实中的种种苦处之后,就会生出要逃离开去的想法。那么,到哪里去呢?当然是要去到一个没有苦痛的极乐境。其时,我们或许都会在心中设定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没有饥荒与压迫、没有黑暗与残暴、没有歧视与争战,每个人都如兄弟姐妹
当乔达摩•悉达多被尊为释迦牟尼的时候,已经是他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了。其时他已然成就一切种智,得大神通,为天人师,于世独尊。这似乎在他的俗名中早有预见,乔达摩•悉达多,意即“一切义成就者”。乔达摩•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现今流行个词叫做“
都说写文章题目很重要,我现在是深以为然的。倘使找到一个好的标题,立马就能吸引别人的眼球,于是也就有了能让人看下去的希望。但吸引眼球不一定就要“好”,怪也是可以的,弄个稀奇古怪的上去,先拉住看客的眼球、也获起了那个让人看下去的希望。为此,我近来也是渐渐有些沾染上这“搞怪党”的习气了。关于这个题目,我想
……或者花儿的绽开是为了贴近你的心那怕只是短暂的一瞬?!……路旁边的那丛牵牛花又开起来了。我是昨天下午才发现它们,当时却在我的心里引起一阵颤,我有些怜惜起它们的憔悴来。在挟着雨丝的凉风中,青叶间稀疏的几朵花儿显得有些瑟瑟的,花瓣都佝起来了,连颜色都也显出萎靡,像是害了病。藤蔓叶丛的底下,还有两朵凋落
我从连自己都很看不起的卖报摊子离开,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这期间,我很到过几个地方,走了几个省份,也换了几份无聊赖的工作,渐渐的就跟先前越隔越远了。倘使要找出那时到现下的联系,也就只剩有着一个对于未来的期待了。哪一个曾经的懵懂少年,不幻想过将来的风光呢?然而,时光荏苒,一转眼七八年过去,这七八年的时光
这其实早经是埋在日记本里面的事情了。我不大喜欢出行,除了上班几乎不出门,按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也可以算是“宅一族”了。这倒不是因为生性好静,其实奔玩起来我是向来没有遇到相当的对手的。我可以在水里游上半天不上岸,可以在雪地里跟人打半天雪仗而不畏冷,可以踢半天的而球不想停,直到一同的玩伴实在全走开,而我
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听说这附近有海的,以前从没有见过,现在似乎有了机会,就很想去看一看。趁了一点闲时,约几个人,化了些车费,去到那个传说可以看海的地方,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附近”不近。不但不近,似乎也看不到海,虽则在路街上穿行的三轮车的篷布上都写着“看大海”的广告,但问了几问,都只摇头,我们就
森林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啊!这森林是多么荒野,多么险恶,多么举步维艰!道出这景象又是多么困难!现在想起也仍会毛骨悚然,尽管这痛苦的煎熬不如丧命那么悲惨;但是要谈到我在那里如何逢凶化吉而脱险,我还要说一说我在那里对其他事物的亲眼所见。我无法说明
我也还是有着不少记忆的,然而,大抵都自己封存了起来,倘没有相联络的物事来牵扰,平时也极少去翻动它们。我很想把握现在,也时时望向将来,以为这于走路与做事都是很有些益利的。至于记忆里的过去的生命,都早经死亡,人又何必化过多的可宝贵的时间去眷念它们呢。而况,即便真要专意的去记忆里面翻查什么,也是很不易的。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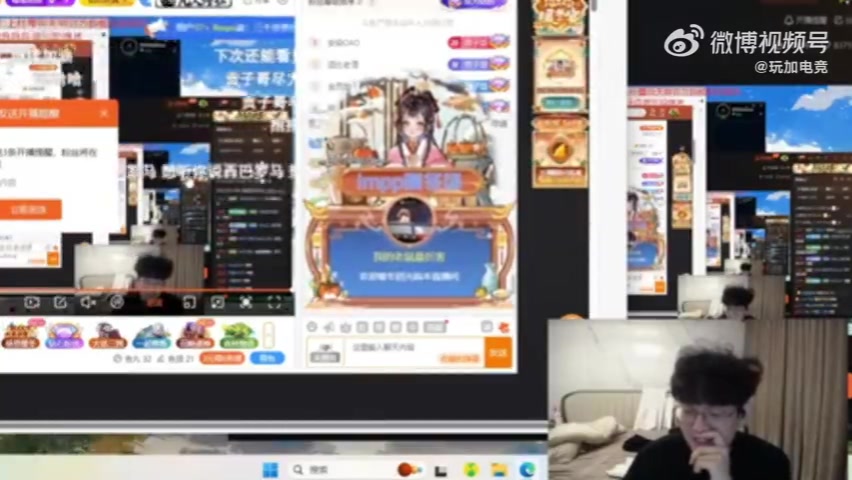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