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扑在水面上,像是困了,准备着要静静地睡去了。在那远处的岸边,零星几座房屋正冒着缕缕炊烟,仿佛正在召唤劳作一天的人们回家吃饭。深秋的江南褪去了酷暑,凉风习习。岸上的柳树枝,野菊花和黑麦草倒映在湖里,就像是生长在水里的,真的一样。一只又窄又长的小船晃晃悠悠地漂浮过来,岳大明悠闲地坐在船上,草帽下棕黑色的一张脸,看上去很健康。他20岁刚出头,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十二只黑色的大鸟整齐地站在两侧的船舷上
人间蒸发一个月的范依嫦去了警局主动承认自己诬告林采菊杀人,也承认自己故意推林采菊下水,她给出的理由是情敌之间的嫉妒,宋利民详细地询问了细节,本来范仓来是死还是活仍然无法定论,所以林采菊被解除了的限制出镜。当宋利民把护照返还给林采菊时,她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终于可以自由了,忧的是倪停雨这个人的手很长,她想起来了,那天晚上,倪停雨曾经对她说过只要她同意以叶千层的名义回到叶家,她可以帮助她摆平一切麻烦,
五十年前,类麻风病在风羊地区流行,其实也不是太严重,但是经谣言夸大之后,人人自危,一时间草木皆兵。“你不要心急,让我慢慢地讲给你听。”倪停雨把一双被子盖在林采菊的身上。那是一个入秋的早上,叶织惠的保姆跟我说几天前她回老家丁山县,老家的表亲收养了一个三周岁大的男孩,那眉眼长得特别像我的丈夫,我当时想反正在家里也无事可做,不如去丁山县看一看,只要有一线的希望能找到我的儿子,我也要试一试,于是第二天我就
年就要到了,烤肉的香味弥漫夜晚的街头,沿街叫卖的小贩,穿着油花花的围裙,肩上搭着泛黄的毛巾。大腹便便的行人,立起了黑色的连衣帽,藏起了满是欲望的双眼。林采菊注视着前方的空气,无精打采地漫步着,不知不觉中她已经偏离了人群,越走越远。她的思绪已经融入了夜色中,在这个容纳一切的世界里,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让人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林小姐。她回转过身,看了一眼,想要确认一下是否有人在
倪停雨已经老了,她孤独地蜷缩在一个35平的阴暗公寓房里,她现在这副模样没有人敢相信她曾经是叶金祥的女人,她不是住不起大房子,她需要的是隐藏,那些厚厚的窗帘就是她保护自己的装备。一日三餐,她在她的狗窝里钻出来钻进去,她不需要每天都洗脸,也不需要每天都在地板上寻找她的袜子,因为她不经常外出。大多的时候,她都是静静地一动不动木头人一般坐着,仿佛那种已经不在人世的感觉,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唠唠叨叨几个人的名字
负责117案的刑警李一凡在会上做了详细的案情汇报,根据现场勘察,死者胸口上的凶器是岳云船家的水果刀,地板上可见一把带血的斧头和一个工具袋,目前推测是死者的,室内只有岳云船夫妇的指纹和脚印,死者的鞋子上套有鞋套,没有发现其它的有价值的线索。岳云船家的入室电闸被拉断,监控器不见了,可能被凶犯拿走了,据岳云船讲,头天晚上8点左右他跳入湖水中救林采菊时,手机丢落在水中,所以他不能收到监控器的报警信号。林采
怎样写小说和故事,我谈谈我的个人想法,其实我自己也写不好,但是我认为首先要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好的小说似乎废话太多,因为要有一些描写,比如环境,心里,动作描写,我第一次看“巴黎圣母院”时我12岁,那时我是跳着看的,一些关于建筑和历史,以及人物的心里描写,我都是跳过去不看,因为里面有好多关于巴黎圣母院的建筑,司法宫的历史等描写,给我的印象是废话太多。后来我又读过三遍,也看了它的电影两次,到现在我也不
也许梦知道她的心思,透过她眼睫毛的缝隙悄悄地钻到她的睡眠里。也许那些圆圆的树叶知道她的心思,一片片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铜钱,她摇着,摇着那早已被人摇弯了的树,她听着,听着那,铜钱互相碰撞而发出的悦耳声音。一声芝麻开门,那些她抓在手里的石子,也颗颗钻石般闪耀,晃得她睁不开眼。在一座金山脚下,漫天红叶,红红的,令人心醉,似一张张百元大钞,层层叠叠,蔽日遮天,藏起了她的脚,吞没了她的肩……她感到窒息,想要大
岳云船善于化妆,但是在结婚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反而没有化妆。他轻松地在几棵还有些许叶子的枫树之间穿行,看到老朋友他会加快脚步,仿佛羚羊一般弹弹地跳跃着,不知道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后天的节制,他并不像大多数男人那样过了50岁就开始臃肿,林采菊在一旁看着他,一时间竟然思绪迷茫,仿佛穿越到遥远的田园牧场。他是今天的新郎,也许是真的感到幸福,他嘴角上挂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外眼角向上弯弯着,穿着一套上万元的
十一月末,晚秋的天气还不算是冷,相比剥落的墙皮和唠唠叨叨的黄脸婆,闲的没事的人更喜欢沐浴在秋日的艳阳中。林采菊就站在一处四层楼的某一个窗口前,她时而沉思,时而向外眺望。风起尘烟,飞落的黄叶,它们没有翅膀却能飞起来,哪怕很短暂,必定曾经飞起过,是的,她自言自语道,我要为我自己架起一做桥。然而,这里,目光所到之处,无论是哪个方向,远的,近得,一律是火柴盒似的窗口,黑洞洞的,再向下看,更无一点颜色。那些
一个阴暗的午后,毛毛细雨无声地弥漫,穿过七歪八拐的巷子,打听一个修理自行车的老人,宋利民和小赵来到范依婵的家,她的丈夫正在做饭,腰间系着一条灰色的围裙。见有人进来,范依婵从容平稳地迎了出来,她的脸没有林采菊的白,显然是经历了更多的风吹日晒,她很热情,嘴角和眼角向上翘着,她并不胖,脸上的肉不知为什么却臃肿着。“您二位是朋友介绍来看货的吧。”她淡定地从一些纸壳箱子中拿出那些瓶瓶罐罐,摆放在桌子上。宋利
最近发生的两起特殊的案子,让宋利民不得不暂时放下范仓来的案子,林采菊的日常活动只能交给了两位年轻警官24小时监控。那两起案子很巧的是,两位受害者一个45岁,一个54岁,两个人遭遇到的情况很相似。宋利民随着孟哲来到了事发地点,画廊小巷15号附近的路边,小巷两排车道,长长的似乎无限延展,古老的银杏树守卫在两侧,宋利民拾起一片落叶,一个小小的扇子,布满了细纹。那边有人在卖彩色的气球,一两个在空中漂浮,也
天气无常,早上林采菊离开丝棉木村时,她心中的希望与阳光融合在一起,形成条条彩色的光环在她的头顶,那光环下的脸白里透红。下午秋雨不停,花草凋零,渐渐得凉风瑟瑟,林采菊的双手和胳膊已经冷得发青。当她被带到了刑警队的时候,已近黄昏。她无需装作镇静,事实上,她并没有太紧张,也没有恐惧,因为悲伤已经压倒了一切,当她想要放弃一切,当她想要和亲人在一起,安度余生的时候,迎接她的却是生离死别。探长宋利民虽然表情严
中秋节过去一周了,10月份的天气不再毒热,也不冷酷,太阳温柔地给人温暖,凉爽的风缓慢而宁静,似乎在人耳边喃喃细语,催人入梦。过去的一个月以来,对于林采菊似乎比以往的两年都要累,好在挺过去了,有惊无险。她把丝棉木村的房子和云海的房子卖了,学校也兑了出去,家长的钱也退还了,妈妈的签证也办下来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离开丝棉木村,再也不回来了,午饭后,她特意带着Andy拐进了丝棉木林,那个她孩童时最初记忆的
一个月的时间,杜夜阑,唐雨前就像两只红气球,刚刚升到空中就泄了气,就好像空气中有上百万根刺,肉眼却看不见,这让林采菊有些不敢出门了,尤其是在夜晚,似乎有双眼睛藏在黑暗的街头巷尾,在窥视她,在安静的地方,甚至她能听到蛇吐信子的丝丝声响,好像就在自己的身后,在深深的草木丛里,在墙脚下的乱石缝隙中。她知道该是她抛开一切的时候了,尽快摆脱目前的环境,包括她的学校,她的熟人,她的朋友圈。可是要走的自然,不能
一场放纵,两败俱伤,唐雨前搭上了小命,周正宣拿出100万免于牢狱之灾,丢了公职,沦落为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个人似乎变成了精神病,他就是唐雨前的丈夫,韩富君。村里人都知道,韩富君有怎样的爱着唐雨前,平时每一次吵架都是她的过错,但是他总是主动示好的那一个。尽管现在她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人人皆知,他还是决定给她办个仪式,他不能让她悄无声息地离去。事发时的那条红裙子已经被血污了,他又给她买了一件新的换上,他
这几天她总是梦见自己变得轻轻地,在空中飘舞,有时她觉得她是蒲公英的绒毛,那周围数不尽的白色,她是那千千万万中的一丝。有时她也化作一缕雾,一点一点地,散做尘埃不见了。有时她似乎看到远处的一团团的什么,像是被撕扯了的蝴蝶的翅膀,所有的翅膀都是残缺的,碎碎的,及其任性,小到不能再小了,没有人,能够有办法把它们拼接成,哪怕是仅仅一片的完整。也难怪,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他们去过山岗上,她的头发上还可见那些被
他不是那种带着花心的男人,也不是那种轻易就对女人动心的人,可是他对夜阑不一样。他的热烈就像一个刚刚初恋的毛头小伙,他的情话每天都来打卡,有时候他称呼她“依依”,他说那是他女儿的名字,他爱她就像爱他的女儿一样,他也舍得花钱给她,夏天的防晒帽买两个,女儿一个,她一个,99元一支的贝儿玫瑰每次送她99朵,钻石从小到大任她挑选。“你这两天和你的丈夫离婚吧,然后我们就结婚,我们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没有人能够认
老胡像一条猎狗追踪猎物似的在屋子里徘徊,扫视着墙壁,一会趴在地上查看各个角落,一会是桌子腿,窗帘后面,大大小小的柜子的后面,他瞪大眼睛,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这里敲敲听听,那里摸摸看看,尤其是凸起或凹陷的地方,或者是墙砖松动的地方,当他把整个主卧室从南到北都搜寻了一遍后,40分钟过去了,他还是毫无头绪。他告诉他自己这次绝对不能空手而归,三年来,他为此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此刻,他就像在丛林中迷了路,
周日早上6点,杜夜阑坐在周正宣的车上,他们正去往林采菊的家乡丝棉木村,她心里知道很大可能林采菊并不欢迎他们,但是她也没有其它的办法,她必须要让周正宣离开云海市区几个小时。前方一片绿色,无边无际的田野在眼前转来转去,时间也已经随着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有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她坐在后排的座位上,闭着眼睛,看起来很平静,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心有多么悬着,悬在空中,就像一只受伤的蝴蝶,拼力地拍打着翅膀,无依无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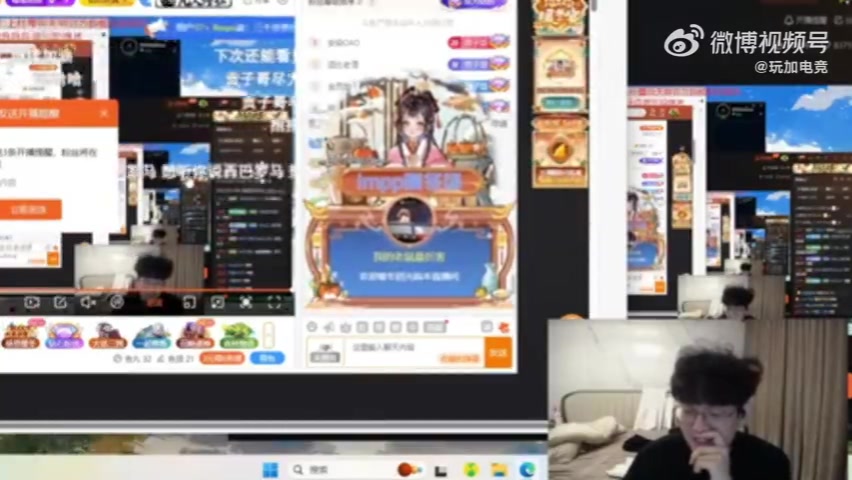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此前称其来姨妈了!朱开向Meiko道歉:用了一个不恰当词语
此前称其来姨妈了!朱开向Meiko道歉:用了一个不恰当词语
 阿尔特塔:我们确信能够应对任何情况,并且会享受对阵皇马的比赛
阿尔特塔:我们确信能够应对任何情况,并且会享受对阵皇马的比赛
 选择贝勒大学!经纪公司:邓雨婷收到60多所NCAAD1大学的转学邀请
选择贝勒大学!经纪公司:邓雨婷收到60多所NCAAD1大学的转学邀请
 曝知名零售商每店只有100台Switch 2:游戏与配件更稀少
曝知名零售商每店只有100台Switch 2:游戏与配件更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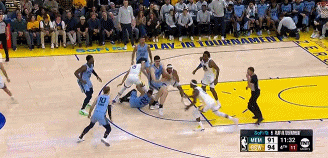 贝恩三分+康查尔反击上篮 灰熊第四节初反超比分!
贝恩三分+康查尔反击上篮 灰熊第四节初反超比分!
 梦幻联动!AL官宣与漫威《雷霆特攻队*》联动:英雄已组团,出道在即!
梦幻联动!AL官宣与漫威《雷霆特攻队*》联动:英雄已组团,出道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