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实的歌声(外一篇)天和海一样的色彩,那散浮的白云是凝团的海浪,旭日在海面上初升,而且西天尚有可见的圆月,如一逝去的记忆,一抹一痕,恍恍惚惚。不,翻天覆地了,应该在大地之上,旭日东升,婵娟依然,白云碧空。我躲在羽毛的下面,是一只鸟儿,不畏寒冷,只是手爪缩进袖中,在街上孤独的飞行。若论千古,惊鸿一瞥;若论时速,千年一瞬。就这样走动,也是飞行;就此鸟毛,也是羽衣。真的有四只鸟儿在我的上边,鸣叫着飞过,
村尾的蓝色星辰不知道是一个孩子,还是少年时期,我跟着父亲,来到农家后院一样的地方,那庄后的浅浅水域,生长着一些参差不齐的芦苇,那高矮不一、扶疏非茂的芦苇竟开满了芦花,不是常观的素白,却是夜空中星光一样的紫蓝,蓝紫的芦花,在无风如画的梦里,让我惊喜,暗暗叹道,哦,这里怎么会开满芦花?这是什么样的地方?竟有一阵芦苇,在水洼,在村尾?又不料,梦后的今日,所讲的课文是《诗经》《蒹葭》,恰好是“萋萋采采”的
吾与草木何悲伤我的那盆文竹迟迟未再萌芽,是肥料太浓的缘故?其它几盆很好。办公室内的一盆仙人掌,像一根棒子,有两尺高,另一盆麻叶海棠,不仅同样身量,而且枝叶繁颇盛,只是与其无情——没有抚育过他们的缘故吧。路边的野花,是一种片片绿叶中的紫色,叫不出名字,却分外的喜欢,也没有抚育过,为什么会喜欢,因为她属于自然,不是谁的私有财物,与我同类吧。还有曾经学校中的黄山栾,开出一树一树的粉红,再逢秋雨淋打,纷落
一粒世界的末日从道路纵横起伏的街市,听到故乡的人们纷纷传说,远方的省份,正有一群高人从那里迁徙而来。他们身高过丈,食量惊人,因为本土资源已不能满足他们生存,水资源匮乏,土地资源紧缺,空气质量恶化,粮食生产恐慌,只好离乡奔此以图存。正在听说这样的困境,却仿佛一瞬间,便看到那通往外省的土街大道上,这样的人群大步而来,他们有着欧洲人的面孔和肤色,其中也有矮瘦而骨嶙峋者同步而行,不断向这里涌来。我看到街道
残联主席孔乙己孔乙己在现代的社会,在现今的鲁镇,是否会代职残联主席呢?据学者王富仁先生对孔乙己的叙事性评论,说自己及一代知识分子,是现代的孔乙己,他们仍然在权力、金钱和劳动的世界继续遭至冷遇,乃至嘲弄与压迫,满颜依旧的坏分子标签,新旧交替出现的伤痕。窃以为,王先生是悲观的,他在沟通了与鲁迅先生笔下知识分子的血脉之际,似乎找到了自己何以痛苦孔乙己的身世,何以触及他们情感的思绪之本。但是,王先生的评述
谁已忘记贫民区我扮演的是从中调和的角色,我的身份是说客。他们两个是朋友,仅因斗气,他必须要杀死他,而且被追杀的人已被困在一个深坑的角落,因被追杀者扬言一块石头砸死无所谓,要死就用一车的石头砸死他。于是,杀人者准备一车的白色石头堆在坑边,两个手下,狗一样蹲在那里。当两方开火,我忍不住大声疾呼,老二,你的魂魄在哪里,快来这里阻止他们。我一边呼喊一个早殇的发小的名字,一边劝说着要开战的双方。但不久,也卷
北京,我念你车从许昌出发,到郑州之后,人一下子涌上来很多,我尚有坐的地方,在车门一侧,再来的人,便挤在旁边站着闲聊,每逢卖东西的小铁车推过,人便被挤弯曲过来,再有些弯曲的躯体发出油滑的声音,让人想到噩梦。这是噩梦吗?从这月24日到29日,我就生活在噩梦里,无话可谈,无颜能说,触及到自己的工作,被他们指谪不断,况且自己做的不已是那样吗?嗜酒扭伤了脚踝,第二天十点才上班,又一次饮酒过晚,第二天刚开电话
用阅读迎候黎明黑暗控制着我的肉体和我的整个世界,意识只一萤火,或者远处夜空里模糊的一盏星,恍然惶然,不甚清晰,类于童年的那些遥远的记忆。那照亮黑暗的光明,我知道,它不是来自东方,而是从声音开始。夜醉晨早醒,既然不能沉睡,索性起来,而朦胧间听到天亮也是光到来的声音,是楼宇一侧的机车声,从远远的地方,仿佛极其缓慢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渐渐高涨,却又在临近之际,渐渐地远去;隔好长时间,又有一辆,和着洗脸时
天天经过,朝暮相随,却没有仔细看过他,只是知道他。今天的这一瞥,在清爽的早晨,却属仔细;仔细在于七窍之外的着想,想到地狱和天堂。但是,妄想之际,知道应该客观的依是人间和现实;这是人间和现在,人间与现在的郑重看待。在人间,赞美过北方的白杨,西北荒漠的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巨树,白山黑水那满山遍野的茫茫林海,甚至南方城市的大小乔木,不一而足。在小城,这排岸边的柳林,本以其条条下垂的统一率,而有南方树木的妩
我的体内是否有慧根呢?只是觉得它在我的体内生长,感到它的力量早已苏醒,正在张望着我心的阳光,吸吮这血脉之里的风水,拓展新的空域,静静而不止息地生长。人声太喧嚣而风中等人的时候,我亦能听到它的拔节声,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好像初次它的力量遮挡住邪光晦气,可以不顾左右,勇往直前,在我的体内生长。于是,我打扫完卫生,照例净食几片碧绿的叫做七叶草的盆花,嗅至田野里最为旺盛的生命气息,然后坐下来,复习昨天收集的
《明史》一瞥粗读《明史》之论,比较黄仁宇先生及旧论之间,前者多有指责,以技术口径测量这个帝国,只洪武一朝,延宕数帝,至居正改革,不能更新,最终匮乏。批评口吻,好似要以西式之科学治国理政方可,中国文化只是缝乱方励精图治,安逸之间便信守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训,即使是边事烽起狼烟,或略有一二,或尚未有炽燃子势,则“未可轻于决战,又不可专于主抚,只是保守边疆、据险守隘、坚壁清野、使虏不得肆掠,乃是万全之策。”
等候我的延续儿子忽然来到,不是冲进办公室,而是冲进这“戒备森严”的人事场所-------我工作的利害之间。我有些窘迫,只好对同事和颜悦色说:哎,孩子大了,家里没人管,只好转到这里上学,上下班接送方便。是的,再窘迫也要把儿子转入就近而且著名的学校,进入好的班级,选择好的班主任。又有更多的解释,无非是自己没有乱用职权,只是无奈的转学儿子的学校。同事们微笑不语;外面肯定有风,那棵柳树的枝叶轻柔的在空中摇
秋天,那算何事儿一位大师说,要成大器,首先须领得烦嚣,受得了气愤,正对于后者,要忍于言,忍于面,终而忍于心,心顺气平,那还有什么气愤呢?是的,至此可以解脱。雪落之时赏雪,大雨滂沱之际,是何等的痛快淋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明白这些。记得是一秋天,树叶黄了落了,寒凉的气息已开始尖厉,在办公室内,一个老同事在众人面前,借故骂人,气恨恨想要动手。而我隐忍着,只能做到一言不发,以至于面露怒色,血气疾涌而
点油灯的老人今天在街上“创卫”,全国性质的,所有的机关人员,轮岗到街头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分到仓库路南段,和一个女同事一块儿。中秋过后的天气渐渐寒凉,但尚无萧萧北风,滚滚落叶,我依然短衫短袖。一侧正在维修的街道,宽宽敞敞洒了清水,比昨天要干净而清静。所服务的辖区,有四个家属院,皆非新建的小区,是颓废旧企业或公司的老宿舍。转悠过来,打扫其中的一个,微微的沙土被扫帚扬起,在灿烂的秋阳之下,不知为何,显现
酒精,酒精一想着寻找那一幕丰收在即的景致,在炎夏之里,傍晚之时,一场南来的风,正在吹拂近黄的稻田和麦垄,远处有林木,万千的树叶欢欣鼓掌,预备为收割麦子间歇休息的人们,撑开巨伞荫凉,万缕细风。我找到了,把它放置在桌面,做我的背景,在我身后的电脑屏面。我也仿佛站在庄稼成熟前的傍晚,在已经凉爽的微风中,眺望我的作品,他们一页一页的展开,在我的世界里,供我的同类我的后人打量,那生长在泥土之中,经历了寒霜和
清虚之街清虚街是条老街,名号不知何年,没有深究,但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常常来往,至此有三十余岁的光阴。现在,与其背后的城河之阳上班,还有我的儿子也在附近上学。下午四点左右,我从局机关里出来,那街北头的两侧,已经摆满牌桌,多是些老人围着消遣。虽然没有喧哗之声,但是秋辉散漫,并不苍凉,甚而有些热闹。也有站在绿化带石台旁打纸牌的中年人,手臂很有力的把纸牌摔下去,狠压在别人的牌面上;更多的是围观的人,一
冷雨夜喜欢黄家驹的《冷雨夜》,不仅是歌词含义,且那种悲情却又宽恕的表达,常在k歌的时候,请求好友们,别唱其他了,听这一曲歌吧。然后在此歌声中,我和他们碰酒,大杯大杯田野里精灵的佳酿,饮进我的生活,生活的情腔,满腔的悲伤和宽恕。昨晚是冷雨的夜,一边搓着麻木的水手,一边对侄子说,中原冷雨夜,冀北春雪狂。侄子抬头看看我,我又笑着解释,咱们这里下冷雨,石家庄基本是下雪。侄子放下敬过的酒杯,摸索着手机自语:
等待“回家”的焦虑头晕沉,秋阳近午,更洒下酒精样的迷惑在整个身心。即使有风,却在听到室外的门窗咣咣当当之时,看到的是满屋满地的风尘,虽不是死水一潭,一切却了无生气。人躲在屋里,躲在能够起身回家的这段时间里,夏午的睡意一样朦朦胧胧。于是,不觉站了起来,在四楼的这间屋内,一个人走来走去。见到窗台,还是原来的窗台,秋阳更暖了,投射到掩蔽的桌上和自己背上,焦虑的心总要沁出微汗一样。想起少年时与朋友的聚散,
适宜我的深秋今天特别好的秋阳,就选择了阳台坐下,先洒些清凉的水在几盆花草之间,端详尤其喜爱的文竹,多少有了枯黄叶叶的模样,可怜之余,看到一月之前萌发的新芽,已经长过了最高的那枝,才放心下来,知道她的生命,即使在深秋,也足够顽强,知道我可以相信,把她接到家中,并没有委屈她,糟践她,害死她--------她是我喜爱的一种女子,婚前没有负累的爱人。是啊,这样的思想或说观念,是不合时宜的吗?我所写的《你们
晚秋三思“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牢记,但在心理上则可以不言自明------凭个人的直觉,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所谓的物我两忘,与宇宙静在万一。”这是朱熹治学“支离”之法之极的宇宙和道德观。相反对的是“心学”,是天人合一观,或者说,是陆九渊批评其“支离”学说的另一种思考捷径;李贽、王阳明一流,与此相对。作为一个简单思考而非治学之人,窃以为,心学的影响要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外媒:亚马逊将打造一部《环太平洋》前传剧集;系列仍有新作可能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Doinb赛后直播聊Tian开先锋撞塔失误:只能说有点高手,老司机啊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2平4负!多特欧战对阵巴萨6场不胜,次回合不胜将追平队史纪录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B站UP发现Tian试图抢大龙遭遇的BUG:有残留视野但无法惩戒大龙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维拉发布对阵巴黎次回合海报:沃特金斯、罗杰斯、蒂莱曼斯出镜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2025币安新手使用教学:从建立帐号/双重验证到买币卖币(图文教学)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Bybit出金方式全解析:加密货币转帐与P2P交易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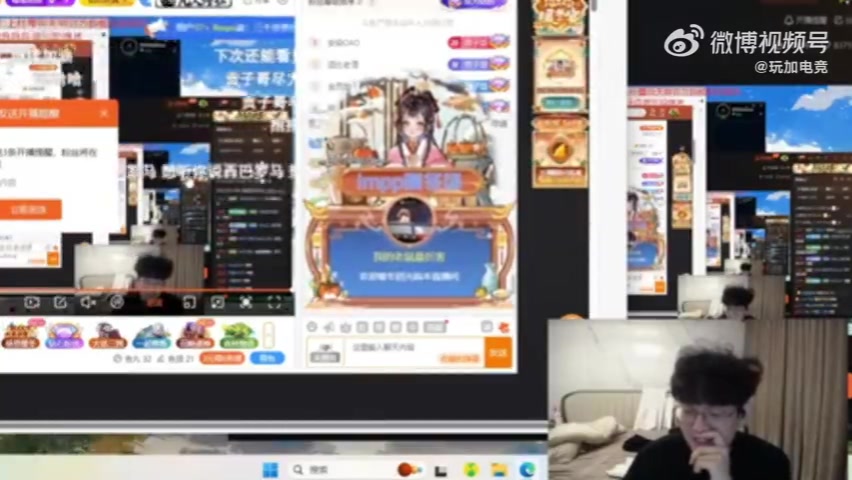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Gimgoon:下次有机会还打老头杯,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
末段狂飙!快船常规赛21战18胜收官 每百回合净胜13.3分联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