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的神话我身在其中,只见圆圆的天空;我说天是圆的。我的周围生长各种食品,荤素渐具。我的家园风景优美,日光和月光投射在水上,一面是灿烂,另一面银华满园。有雨斜至,点无数的圆在我家的周围;有风相约,携带另外的种子洒在我宅的四边,能成活长出一株两株,诱引飞动的肉食落网,供我美食美餐。我脚下的水域,域中的泥土里,有人称为龙蛇的蚯蚓,那可是到处游动随处可捕的,为我所养的鲜活肉食;吃蚯蚓长寿。也有更大的更新
握住花园里的在咋见是不显明它们的衰微的;花还在开放,有童掌大的好像叫做大理花的红,开的最艳,虽无香味,却有一只蜂嗡嗡的在丛间飞舞。沿石径走几步下来,踩着地上野草,去看另一朵最为熟悉的红花。她一直未隐其身,并不为人等的光临,本身她已澄明,在夜里做着抵抗和准备,因为抵抗而高傲的预备;阳光朗照之时,澄明打开,像她的花瓣一样伸展。我的到来,只是成为她的澄明的一部分。我的思绪嗅近她的花房,听到里面淡淡的香泽
朝阳在手掌中升起昨天是无意的一瞥,那轮红日,在东南隅的一角。今天,特意的看它,哦,它变得微小,但红彤彤的,在苍茫的晨霭之海,朦胧而遥远,梦也无法比拟。那沧海就是沉沉的黑夜吧,那梦在黑夜里妩媚的航行。是啊,如果,我不去看它,又要错过此轮朝阳了。酒醉的时候,势必是要错过朝阳的。醉里子夜方眠,次日昏昏沉沉,噩噩浑浑,起床后,太阳已升入高空,秋晨的俊爽,林叶的雅静,都已经过了时点。那样头昏体乏着,被肉体之
我家儿子要会考躺在儿子的床上,透过他朦胧的蚊帐,看到远处的时间,不再是梦中的死亡向我微笑,却依然悱恻的自问,这是我的家庭吗?儿子今天很懂事,刚起床就开始复习,但脸亦未洗------这是我的过错,为什么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呢?起床把每月应给的二百元钱,轻轻的放在他桌上。他没有说“谢谢”,也没说:“你也起床了?你吃早饭不吃?”然后我打车到工作的是非之地。这不是悲哀是什么?儿子也许考前压力太大,凌晨起来到
一个寻找权杖的幽灵当我试图沉浸在关于国家何以凭血统和文化凝聚民族力量的时候,由于它的苦涩和遥远,那些耻辱的历史和仍然不断的纠葛,不时闪过我的脑际,逼我烦乱,不能自已。但那些文艺的难题或疑问,是自己该去了解的吗?该去寻找答案的吗?我还是当年的幽灵?我是否能够成精?外面的风声渐紧,仿佛要天变迁,又何以能够慰藉我度此“难过,”回到平静那理想的生活?而又有谁否认,这样的生活不是生活,期间不曾含有幸福么?期
游禹州周定陵周末到来,我以为约友携子去别的,朋友却说到外面走走。外面是出市区了,而且禹州,早先称为颍川的所在,大禹开山导水之经过,那当然好,就领着儿子去游历一番。三家人坐齐,出市区后也未定好去禹州的什么地方,电话询问那边接待的朋友,安排上午无梁镇,下午邻乡的一座山峰,实际上是整个伏牛山系的支脉,具茨山的其中一峰。下午的爬山,我没有爬到峰顶,不如两个七岁的孩子,只是坐在山腰,沐浴鼓荡的缕缕不断的山风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她一边试讲,一边抹开了泪。她讲的是生母,质朴的人质朴的演讲,迅即回到往昔的岁月。五六个孩子并不是哺育长大的,母亲是驻村干部,下乡去了;退休后的母亲又组建“老妈妈服务队,”为社区为驻许部队发挥余光余热。讲到这个家庭,整个家族,培养了十几个成功的学子,优秀的人才,颇为自豪;当讲述她为年迈养母亲手疏通肛肠,又情不自禁,泪流脸颊。”这是一段昨天的演讲,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同事介绍,要给这个演
疏离------儿子的受伤他“呀”的一声,我在厨房听到了,急忙跑出来。见儿子双手捂着脸部,痛苦的起伏着身子,难受的呻吟。我惊讶的问:“怎么了怎么了儿子!来来,坐在这里,让我看看?”银色的光下,一股鲜血,从他的额头迅速流淌到眉目。我反身快速拿来纸巾,帮他捂上。他的泪水同时流了出来。我严厉的说:“不准哭!怨谁呀?不是让你吃饭吗?你说亏不亏?”我怒斥着,想到幸好没有碰到眼睛,但创口的大小不清,便又说捂着
反刘邦的密码这几天里,刘邦总在我的侧面出现,其先“威加海内,安得猛士”《大风歌》的正面形象是主流,是一代帝王。在群雄四起,天下震动,四海纷乱之中,树雄心,攘诸侯,百折不屈,屡败屡战,终于打败项羽,建筑汉室,巍巍于两千年前。都知道。九州血腥之土壤,滔滔历史之风浪,间或传说着刘邦的流氓,比如说《高祖还乡》之类,是更多了些贴近事实的遗闻,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吧。而近几天来,随手翻看几页《史记》,看到韩信、
三棵树也许我守望的足够,所以,我以为她也在望我-----那单位门口左侧的三棵树。寒风中我望过她,冰雪中我见过她,始萌褐黄嫩叶时的初春,我从她青春的身影里,打量着她的活力、勃发和性趣。她也常常经我四楼的窗口,回首望她之时,也那么沉默的,却又微笑着或矜持地看我。我以为她不是谁亲手栽种,从幼苗,到少年,数风雨春秋,而又如此高挑的身躯。我以为,当她还是一粒种子,一株最小的幼苗之时,就开始酝酿着自己未来的理
小巷的苔痕“你能不能把上面的绿苔采下?”“我看不到。”妻子又说:“那下面的不是?”仔细去,是墙根的地方,一尺之距,长满了青青的不似周围杨树颜色的绿苔,碧绿一些的,淡漠一些的。“苔痕上阶绿”;有人,心旷神怡。这是一条我们不常走的小巷,在小区的南方;雨的巷更是少人观瞻,少有人往。不,也许这里住家的老人,有自己禅意及清净的生活,是这里名副其实的主人,不是匆匆过客。你看他,老人家,站在低矮宅屋的门口,轻声
回头看她,阿莲八点要开始的晚课之前,勤奋的学子已经坐满了教室,窗外的夏风,不时一缕缕的进来交流,不断疏散着白日淤积的暑气。我坐在倒数第二排里面,忽然觉得熙熙攘攘的班级有些异样,不觉抬起头来,哦,教室前门处亮闪着,是一个高挑身材、皮肤白皙的女孩儿,站在暗红的门框之间,向教室内打量。教室内的窃窃私语声,看过之后,又渐渐的起来,而女孩儿移走而来,不去别处,竟站在我的身边。“这里有人吗?”“没有。”我很平
春,是清静的语言不知在这春里,为何有些眩晕,这春的气息里弥漫着一缕一缕的倦怠,迷惑着我,消沉着我,这与每晚的耳鸣和闲光中的木讷是同一幅毒素或蒙药?这是什么春?这哪里是记忆或传说中的春呢?枣红色的书案,在各色或暗淡或幽明的光里,我翻卷着手头的笔记和书籍,无论是刊物还是文集,是古典的诗赋还是魏晋的人物,总归找不到那些解脱的纠缠的头绪;关于春和春天。无以逃计,拿过一摞作业,翻看孩子们的日记和随笔。而那如
一家人的逃亡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有浅蓝色带紫的花,在路旁点点染染;我在刚刚铺上油石黑漆一样明亮,六车道一样宽敞的大道上行走,那是一条通往乡村的河堤之路。那路旁依稀还有一丛丛悠闲的柳,一坡坡融杂的草。走在那样的图画里,还记得自己在推敲字句,像在键盘上的手指舞蹈。而不久,我们一家人走在另一条路上,从不知何处的深处,赶回到这一条土路。所以当我看到危险的时候,情急之下,让他们母子隐蔽在路侧的沟里,那里灌木狂
昱弟归来一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海军军官的成长史,也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人怎样毛虫变蝶,飞离窄暗的故土,美好了自己的人生。十五岁当兵,没有过去的长枪高,肥大的绿装罩在身上,集孩子与军人的身份于一体,谁见谁怜,忧心临渊。但他就是要走出扭曲的家庭,要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是什么样的家庭?十二岁,刚上初中,父母数年吵闹,终究离异,在一个仿佛悠闲,却遭大变故的暑期,他要离开他的母亲和兄长,和他的父亲单独生活了。而且,
苍茫的灰暗地带阳光与死亡一样,概不必凝视。鲁迅先生则说;“惯于长夜过春时”。于是,预备了一个文集,或者长篇的文章,曰:《夜记》。有人说,“夜”是永久性的记忆,所以是永恒性的话题,是“光”同样重要的生与死的话题,而且会穿透生死与明暗黑白,永远固在,所以要像歌颂光明一样歌颂黑暗。是吧,没有光明无法孕育生命,种子不得萌芽,枝叶无由光合。但是,没有黑暗,同样不会有生命的孕育,生命的成长;大爱无言的黑暗,默
一地怨声咣当咣当,风吹着关好的房门,不时咣当,在晨睡的朦胧中。起床看时,原来外窗被家人打开;但,今天是个晴天。早五分钟上班,或者说,晚十分钟上班,因为步行便晚些,骑城市配备的公用小绿车则宽裕。骑车慢行时,一位棉衣围巾口罩严实的妇人,在后面过来说:“这孩儿!”怨声我太慢挡道了,有些咬牙切齿。她不知道,我心平静而去望了一眼广场边上的那群舞者。那是八九个少妇的广场舞,果然于此晴晨在舞动;乐声隐约,毛衣窄
待宰之鱼的告白鱼的寿命有多长?多数人回答不上,我也只能固有叹息的扭回头,却总是问不明白。大家所见之鱼,多是被空气所缚的,困于器皿或刀俎的,因此很难知道鱼的自然死亡吧。鱼是怎么自然死的呢?没有见过老死于渊的鱼的形状。据说,大象知己大限将至,便会步出族群,寻到他们隐秘的墓址,悄然长逝了。那鱼可否也知道自己的大限,也有自己的墓址?一个人推测对我说,鱼的死亡是钻入水草窝内就死了的。这话常常漂浮在空中,没有
一个男人的薄雪晨前,中原之中的城市,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拥戴着万千的素华,在冷绿的麦田之间;也掩盖着道沿,那些枯黄的草叶草根;雪白地镶嵌着,那潮湿黑色的笔直路面,如淡妆的处子,或者年轻的少妇。上午九点,一轮桔红的月亮,不,像桔红的月亮一样,轮廓鲜明脸庞羞涩的太阳,在浩渺的东天升起;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帧照片,可以铭记而回忆;一枚红玉,足以时空瑰丽和魅力。我没有动她,没有去抚摸,我甚至没有站在走廊专注,只
冬天的柳阴郁的天气,无雪也无风。早上上班,步行最为相宜。走出十五分钟多些,身体内分泌的热量及所谓的某种元素,不觉缓生人的兴致,浸出什么神秘。正好走到湖滨桥头,听到几声鸟鸣。举头眺望,是远处桥头的一棵柳树上,有四只灰色的鸟雀,在枝头顾盼啁啾。柳枝已褪去叶片,稀疏的柳枝间,灰亮的天色里,点线相饰,竟是一副有些熟悉的画作。那是一棵中年的柳树,树干并不粗壮,而西湖公园内的垂柳则坚实硕大,大多合有两抱,树桩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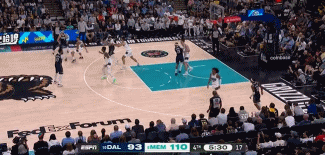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