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灞陵桥揽胜诸人,无论是在深秋,还是在初夏,只能在传说中的桥址堤口处,望着铺就两岸的水泥桥板,听讲解人勾画桥的原貌,口传越千年的挑袍逸闻,和诸多另存的信息链接粘贴,而浮想联翩吧。春水荡漾,秋波依依,因为关帝庙虽存,旧石桥却已经湮没。堤柳逢春,却又深秋,风暗尘旧,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许昌关帝庙,在许昌市西郊;传说关羽挑袍辞曹的灞陵桥,也在西郊此清泥河上。寒水潇潇,春寒酷暑,二十年间,所知道的
铜丝捆绑的国旗早浴过后,透过卫生间百叶蓝窗,我看到向下伸展的那条大道上洒满阳光,是个暖晴的周日,野外的油菜黄花,想已开遍了吧,那清新的空气,那空气中飘荡的花的香,和那春天特有的醉意,还是那般美好吧。应该践行此旅,出去走走,也可以心灵放飞,去游览观赏那神秘的大地和气息,还有那里的河水,水边的垂柳,垂柳边的女儿,我的朋友。阳光已经透过儿子卧室的窗帘缝隙,落几片奇丽的块儿,在不规则的床被上起伏。儿子出去
邂逅微笑还是启明步行的途中,我和儿子踏上了歧途,要与我的朋友们汇合,必须从高台上爬下。我拉着儿子帮他,儿子大胆而安全的落地,我却回到了童年一样,惊恐中不敢往下攀爬。就在这害怕中,一个电击一样的痉挛,自己猛然醒来。少年时高楼悬梯上的惊魂烙印,在沉梦中焦灼。但最为惊讶的是,自己的梦里总是在路上,路上遭遇的总是险情。往往有美梦的开始,途中却险象环生。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少年觉性的年华,曾经在南关大
黎明的邀请园中万有的晨光,淡洒在葱茂簇簇的林木;坛内闭合的花草,微漏于寂静未醒的笑梦。最早起床的鸟鸣,在银灰的光亮中,翔入清澈的眼界,如南国丽语,零星呼朋,终降在高高如岩的窗台,寄情黎明中的山谷溪流,给睡着的孩子,和那渴望的眼睛。高高欲倾的山崖,秀容挺拔的青峰,崖头迎客的松柏,崖壁岩生的奇葩,和着晨光的相拥与俊朗,和着林烟的缠绵与飘逸,孕育着大地深处的甘泉,沿着蜿蜒的地线和高山的血脉,一路汇集着草
谁的目光是慈悲我们听得懂他们的歌词,更不用说他们的心声,那艺术与情感是无需语言的,是超语言的。他们在歌颂两国的友好,欢唱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的相聚的快乐,欧洲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友好交往。我盯着他们的面孔和目光,审慎着他们杨杨洒洒的神情,不知为何,在电视面前,在他们精彩的演出之间,流出了感叹的眼泪。我知道眼泪是怎么回事儿,我知道那是历史的恩怨,往昔的耻辱和愁苦,耻辱和愁苦所映衬今朝国运昌盛的感动。那深眸
胎中之钉风被山崖所阻挡,我们是看不到的,只是在其历史演变中的一个千年间,或者一万年看到风顺的一面是斜坡,逆风的地方成为绝壁,因为风力是以千年或万年以上显现的,而山是风之胎的钉。摩托在风驰的时候,听到风的声,是自己制造的气流声韵,与风有着极为贴切的关系。我知道它,所以中午下班之后,就用很快的风速,急忙回家,可以见到儿子,又可以午休片刻,可以离开繁杂的人事,回归原来的生活和自己。我的摩托以风火轮的速度
把时光埋在鸵鸟里原来的旧居,租给了一个刚刚上班的而学生,虽然一再短小的交往中,见他骗过了中介,让人感到他的不够诚信,却仍以为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便不计微疵,与他成交。但果然,那间小小的套房成了我生活的负累,他常常出差,接连出现了两个差错,说好半年,他预付房租500元的,却因为我轻信他的诺言,怜念于他刚有工作,就答应他只交了一半,后一半过一月再交。届时,我踏着并不美好的夜色,在晚课的忙碌之后,一
一月走在路上一个人走在路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十岁,即几十年前,一个孩子起早贪黑,常常独自在路,早上前往城北的学校,晚上返回城南再南的叫做水泥厂的家属院,曾有的家里。现在,几十年之后的每一个季节,我一个人走在路上,何以这样沉静,也许就是少年时期锻炼磨砺的那种思考方式和行走能力,那种独在的冥想习惯,奇异的行走方式,一直在身,至少重归本身。于是,一个走在路上,就是思考与冥想在那人群喧闹,却又能够僻
我们照亮了焰火原先小区的那些桃花,已率众红遍了整棵树木,不仅是楼下花坛中的两树,在小区的中心花坛,更有三株最为盛茂,那深赤而非与浅红的,静静的在那里开放,鸟鸣声声,使我知道有不知名不见影的鸟儿,隐身在茂密的枝桠和鲜花中,使我清醒这里的气息净洁,鸟儿可以安家、生活、欢唱嬉戏。鸟儿当然会选择这里的宁静,这里的场地,和小区的居民和谐的共在,在场。滑着轮鞋的儿子,已经飞到好远处,喊我要出发了。我们约好,到
梵高的几缕眼神《吃马铃薯的人》是很丑陋的,那早期的注视和眼神,却已透漏出梵高不凡的气质,那独有的氤氲。几人围在阴郁的灯下,因那些人神奇的各异表情,想起朋友们在一起吃饭的情节,清贫人家围炉静守的往昔;那些情节流洒诗情,那些往昔泪花绽放。《盛开的桃花》是别与东方的风采与花样的,因为这株桃根略细,而主题灿烂漫天,满载了人的视野,那画面,天空云翳,却因此有了色彩;恒星没有出现,没有人影,却看到太阳普照了物
一粒生命的冥思那是一片冰雪的世界,有枯黄的被雪掩盖的衰草,有冰结冰片滑寒的青色石板,有不易攀登的高高方台,还有石栏镶嵌而弯曲的河流,幽幽的散着微微寒气的河流,还有不同的树木,成簇的开着白花一样的灌木,成林的树树梨花一样开放着的乔木。隐隐约约,我听到那高台之下,雪草之上,石板之旁,传来一个妇人的颂唱: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怜
武汉大学的惆怅思前想后,并无惆怅。恍惚之间,听到那幽暗的黎明之前,有泉水流声,渺渺的,细细的,似存似无;渐听下去,若雏鸟的微鸣,确有泉声,却如泉水流淌般的鸟鸣,那就是黎明将开的呓语。果然,那声音大起来,清脆的,流淌在朦胧中,婉转的,三四个音符,然后是那种依然熟悉的,有些单纯的两个音节的那只鸟儿,声音最亮,似乎是想和他们,对鸣着不下四只鸟儿的啁啾,共鸣在我们的窗外。我知道,天亮了。稍抬起身,见我的窗
端午的苍天,把亲人祭奠那是4月2日的一个上午,灿灿的黄花已经开遍了原野,母亲故乡的墓园中,处处高大的坟墓,莽莽榛榛,长满了碧藤和芳草,春光明媚;郊外的苍苍长天之下,一方温情脉脉的水土之间,微微的风中,空气中飘散着泥土和花草新鲜的气息,重归故里。我先回姥姥家,去看了垂暮的大姨、大舅和大妗,才来到墓地,看我的两个姥姥。我买了一只鸡,一剖两半,分送给他们,带来乡下不常见的菠萝,一圈一圈的剥开,还有刚才买
阳台密语太阳被春天的漫漫风尘席卷了,抹去了它原有的光辉,只一面银镜一样,挂在四月的东天;连镜子也不如,浑浑噩噩的,不看不见,你也可以视而不见。所以,阳台上的杂物闪亮起来,纷呈它们的色彩,而且听到它们的密语。一只我常坐的木质方形靠椅,其上堆满衣物,有待洗的棉袄,叶绿的毛衣,妻子枣红的外套。还有儿子似乎还散发着爆竹硝烟味道的新装。把他们挤一挤,就可以坐下拥护着坐下。这只橘黄色的椅子,是在旧居中搬来的,
晚安,夕阳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新奇的,像一个孩子,至少是青青的年;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新奇的,像一个春天,至少是微笑的颜。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新奇的,都应该是新奇的,因为你热情饱满,你工作顺心,你的能力正得到公认和肯定。所以,在人流涌动的大街上,在奔赴友人的约会的途中,正西风,到夕阳,如此神奇,如此美丽。因为夕阳她足够饱满,巨若灯笼,在街道的尽头,在仿佛我一人的视野之中,如画如诗,引我暗暗赞叹。是的,我是赴
隐私的河流月末到此,已是初春的雨歇的傍晚,浓云团团向南天散去;河流正在回暖,泛着微黄的绿,同样向南,暗暗地流涌。那河水是微漾的,跃动着的,又是自顾自喜悦着,也仍然平静,在空无他人的春堤之间,多像一条人的秀眉,时尚女儿的翠眉在爸爸的怀中,那么自足,那么平静.河流也染着堤间的密密幼林,泛着微末的黄,在未夜的天光下,在一夜半昼的雨后,涤尽了它们一冬的枯黑,也本质是那土地的深处,与河流脉脉相通的根系,闻春
公鸡要详细地占有资料刚到这个机关不久,新同事们以为我坐得住,特守时,那么埋头不知疲倦的看啊记啊,以为我是什么优秀的人物,背后夸,当面也以为夺饭碗的人来啊。他们的谨慎不是多余的,虽然他们占有春天,发梢翠绿,脸色旭红,却皆知此季,你不生长,他要生长的----这是万物萌动,万生竟长的年代。可是,他们的确高估了这个新来的,也许不久可能又被派遣回去的同事,因为,我常年在基层工作,对机关的作风、业务及传言中的
沉默是最大的声音周围的声音太够复杂和繁多,寂静临时,我们又已休息沉睡,好像到处都是喧嚣,早晨的太阳和上班的人流,傍晚的暮色和各种车辆、人颜、谈吐,在各宾馆酒店的灯光前,交相辉映,好像这一切表象就是世界的本质,没有大地、海洋和宇宙。宇宙应该有什么样的寂静、沉默?每当夜晚来临,深入到人静之后,我们才看到宇宙真实的一面,看到沉沉的黑夜和寂寞;宇宙沉沉的黑夜,人的寂寞与孤独,才仿佛见到世界最为真实的一面,
曲径通幽处,春花开人家昱弟无意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至今,也会继之一生,因为那不仅是对一种植物生长习性与优质根性的阐释,而且他们的品相和情怀与自然相关,与人生相系,与化境相通。所以,从那之后,总是关注这样或那样的植物及生命。那是年前,乡亲送来好多蔬菜,其中有儿时常会吃到的,叫芥疙瘩。这种菜被乡人切成细丝,灿灿的阳光下,白花花整席晾干,多在老坛中腌制。它有特殊的品质,贫寒人家是家常菜,因为这种菜的腌制
人何以成神当他的肉体已经彻底消融,包括他的骨植,他的衣饰;他的历史与英名,却千古留存,不是口口相传的故事,不是笔墨未干的传奇,奇特的似乎无法概述。他的事迹或伟业,超越人的一切,人的一切的经历、实践和总结,他成为超越者,不朽者,这就是人何以成为神的不确定义吧。这样的问题,曾经围绕着我,在我思想的夜空,遥远的星辰一样闪闪烁烁,半年不去,模模糊糊,不通不克。桌前坐的久啦,眼眸苦涩,思维迟钝,便在初春的走
 手游《怪物猎人:旅人》微博账号开放:发文庆祝获得版号!
手游《怪物猎人:旅人》微博账号开放:发文庆祝获得版号!
 最强RS 6 Avant GT来了 限量66台正式开启预售
最强RS 6 Avant GT来了 限量66台正式开启预售
 说唱歌手&演员宝石老舅喝酒闹事被抓:释放后发博道歉 直言酒后失态爆撞路边无辜车辆
说唱歌手&演员宝石老舅喝酒闹事被抓:释放后发博道歉 直言酒后失态爆撞路边无辜车辆
 高速端到端 /AI 推理可视化上线 体验理想 V7.0 版本
高速端到端 /AI 推理可视化上线 体验理想 V7.0 版本
 索尼蜘蛛侠宇宙新片接连暴死!高管认为质量不差,还甩锅媒体
索尼蜘蛛侠宇宙新片接连暴死!高管认为质量不差,还甩锅媒体
 2025款腾势D9正式上市,售33.98万起,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2025款腾势D9正式上市,售33.98万起,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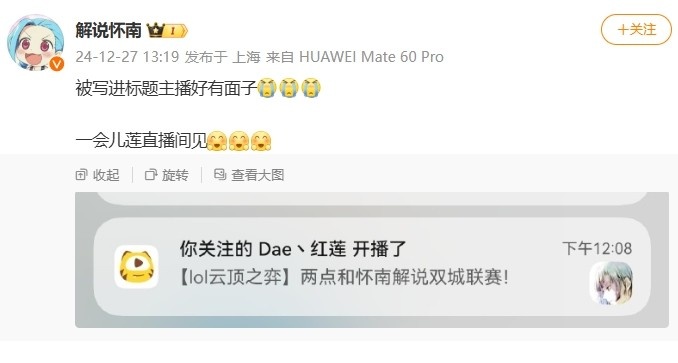 解说怀南:被写进(红莲)标题主播好有面子,一会儿莲直播间见
解说怀南:被写进(红莲)标题主播好有面子,一会儿莲直播间见
 朗逸NF/途昂PRO将于明年推出 奥迪A5L年初发布 AUDI新车年中上市
朗逸NF/途昂PRO将于明年推出 奥迪A5L年初发布 AUDI新车年中上市
 美国专业健身教练怒斥贾玲体重反弹:“秘密减重”搞的人尽皆知 全是围绕“减肥”的营销
美国专业健身教练怒斥贾玲体重反弹:“秘密减重”搞的人尽皆知 全是围绕“减肥”的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