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向西倾您是何时对命与运生畏的?三十之后,我便开始了。比如让过世的亲人庇护我的娇儿,保佑我的事业。大年初一的上午,窗外爆竹声声,雪寂无风,一派祥和,我郑重其事的祭上贡品,两枚红色透着秋黄的苹果,一碟自己煮制的牛肉或者其他,然后给她上香,不仅鞠躬,还上三柱,断香不用,那么虔诚,青烟袅袅。所以,与此相关的一切符号,都让我常常痴呆思考。我的名字有一个“旭”,“旭”是什么?是东升之日,只有在东方才有
善良的公文早春的风,不记的是否料峭微寒,办公室内静悄悄的,只有翻书点健拉抽屉的声音,却小过于远处街道上驰过的车声,因为旧历的新年只是第九天,应是上班时间的幽暗走廊上,还无人走动,可以来此办公的人们,料不到此处的工作人员,早已到齐,也不会知道,有新的职员刚刚到此报到,以最春天最旭日最年轻的朝气,奋发勤勉的工作。办公室有五台桌案,上面摆满了几年来于此科室相关的文案,那高级到国家,基层到学校的各种事件,
训斥清晨何以堪夜晚是属于自然的,不,是更接近自然,按照自然的本意,那一切因此开始沉寂下来。光明收敛,让我们看清那夜空中的星辰;大多的生命开始变得安静,闭上眼睛,放缓血流,开始修整;或者已入梦乡,乃至一夜无梦。清晨,因此支持新相新生。天色渐渐亮了,银色的黎明在朦胧中,在窗帷苏醒;听到不知名的鸟儿,一声接一声,在歌唱黎明。站在凉台,在晨曦之中,阔阔脊背和腰身,深深的呼一口气,空气新鲜,一切都显得那么纯
两株碧树为谁栽2月22日,浓浓的雾,在昨天的早晨,弥漫在中原的两方地域,曰禹州,曰襄城;天气突变的预警之声,从巨大的银屏上滚流而过。果然,今天的早晨,此雾从八百里伏牛山脚,从禹州襄城西来,上午近十时左右,缓慢散开。推窗远眺,见那窗北正在建设的帝豪广场,雏形已就,虽有废墟留存,却大势所趋;若待此春回归,那广场之上,必然绿丛花树,明媚游人。所以,此时此景,其情其思,不由想起故园的碧树,一株,还有一株。
我的百合我的梦------致乐恩教育集团十年庆典一当银色的黎明从窗帷的朦胧中悄然苏醒当圣洁的百合在我们的心田里睁开眼睛我的孩子2005年五月的春光从中原大地神秘的方向照耀我的生命我知道,有一个梦想是那银色的千年不息的长风我决定,我要建设一座城我决定二那是一个悄然而至的银色黎明有几颗星辰依然闪亮着神奇的眼睛朝霞映照着中原古老大地的风景是我的孩子刚刚睡醒我决定,我要建设一座新的城在千亩游园的绿风河畔在
苍松下的客人当我隶属的这个城市,小城市不断萌发出新的才华横溢的艺术人才,尤其是文字工作的作家,我会嫉妒、内疚、感叹,自省和奋发吗?我被那些真诚、美好、善良和魅力一个又一个打动,却忘记自己也应该用真诚去塑造,去告慰已经失去的青春和岁月,自己的灵魂。而眼下,天空暗淡,没有风云,面前和左右,没有令人欣慰的文章和情怀,一切仿佛停留在这些生活的外面,只能观望着别人的情怀和塑造,不能登上舞台公演共荣。一天工作
黎明的曙光透过窗帷我的心近来并不平静难以入眠,黎明即醒昨天的冷嘲和热风在床榻周围,纠缠不清今天还有什么是非今天还有什么要面对黎明的曙光透过窗帷曾经的日子那么平凡平静曾经的夜晚无梦醒来或者是甜梦相随我的心近来并不平静难以入眠,黎明即醒昨天的鄙视和面孔纠缠着我的是噩梦黎明的曙光透过窗帷我知道一切都要面对不管谁的是与非依然坚守自己的堡垒依然求索真的善的还有美依然把理想去追
孔尚任的飞天晨阳换晓日,别是一番轻巧;夕阳做了落日,一派悲壮,瘦马古道。全凭心情,仅因眸光。早上,站在阳台,望丹阳初生,嫩光普照,迷雾如海,不觉情动于衷,想起“山松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桃花扇》,一声一曲高,再有残花败树,腐李朽桃,在远处隐约可看,不由翻看李香君、孔尚任、《桃花扇》,读兴亡之事,感离合之情,旅其意境,启发悠悠不尽的漫天光星。
这不是泰戈尔的传说你知道你的手机和儿女的眼睛,手机和眼睛都是会发光的,但你或许不知道,你家的墙壁,你的饭桌,你的一件衣服,特别是伴随你,为你遮风挡雨,为你展风度添风采,伴你很久的衣服也会发光,而且说话。它们,你不留意它们的时候,它们一直保持缄默,暗淡着隐匿着蛰伏着,等待你的逝去或者被你抛弃而死亡。但这丝毫不损它们曾经丰富的内涵,它们潜伏的呐喊或者低语,它们盒敛的光辉或者芒刺。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注意
粗哑的售票女孩儿我没有去看她的长相,即使这一路郊区的公共汽车人员稀少,但我熟悉她的腔调,她说话的声音有些粗哑,我搭上了她的车辆。我不顾车窗外料峭的风吹进我傍边的车窗缝隙,不顾春天正从不远处呼呼的笑着,孩子一样打闹着,我发着短信,敦促要开展的各项工作,却在这忙碌中,在春天到来的路上,分明知道所坐的这班车,是她的车辆。真正与她打交道,只有一次,他们车到城市的汽车西站,在人员已经密集的杂乱中,忽然停下不
桃园密言他悠悠发声,密音般传来。“这里,应该复色”。于是,第二年的春天,这个废弃的园子便开始涂染绿色,堆堆灰石破烂的周围开始长出青草,高压电线的铁塔上,不知什么时候筑巢的一家乌鸦,见此春天于楼下缓慢而巨大的展开,也息音屏气,安静服帖。盛夏之后,还会有牧人和他们的羊群来此,闲聊散步,自由的吃草。他们听到神或者主或者上帝或者谁的召唤,那谁,用密语告知,在浓夏之前:来,这是你们的门,你们的家园,可以进食
旅途呓语一我们离开城市,却无法靠近四野。车行之处,窗外不是小镇,就是都市化或市郊化模样的村庄,庸碌的房屋碉堡一样的房屋,庸碌的工厂塑棚搭起的工厂。我们离开城市,同行的旅人,有的可亲可情,有的充满斗志,喧嚣嬉闹,恶意来往。而在独善其身,神驰境外之际,我们的车速渐渐放缓,又进入另外的城市。这个小小的城市,印象仍然不好,混乱的街头,混乱的交通,不洁的容貌;上来的旅客,嘈杂的议论,让人想到国内遭遇的流言,
我的雪园,梨花开早晨上班之际,黎明之前的天空,飘下微微的雪花,只是刚刚落地,就神奇的融化,没有踪影,只有淡淡清凉的味道,融化于周围的气息;更不会邂逅来往的车灯炷上,飞舞着那冰凉的素花的影,曾经雪在燃烧的旧梦。而且,在略显焦急的等候公交之间,东方渐渐亮了,神秘在恍惚之间隐形了;到了郊外的单位,整个院落里潮湿迹象也无踪,更逊于市内之间的多情。想到一个人在公众的场合说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好像他真的达
一夜无雨也无风-----清明,想念母亲那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杨树,又查字典,知道是普通不过却又常常忽略性质的毛白杨。这一棵在上班的途中天天相遇的毛白杨,在许昌市医院的南门东路上,人流奔涌,她兀自挺立,有点儿悲壮,因为若有人能关注她,也是因为她清高的干枝蓬勃到高架的电缆电线,他人以为危机,比肩斩断她的风姿,兀自成桩,笔直耸立在人流中间,那医院矮墙一畔。但是,春天来了,就是这样的她,在习习的春风里,却生出
邮递的花祭国人是含蓄的,平素的日子,不大愿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意,那内心的真诚,也许他们只是抬头望一眼略微想一想,那灵墓高高的碑,内心的祭奠便已经开始,就像内疚便是祷告一样,不必专程前往,不必献上鲜花。只有在非常时期,我们才会激情感动,把无限的哀思,忠勇的意志,制成标语横幅,编织花圈花篮,雕饰诗词歌赋,贡奉于碑座的四围,游行在广场的北端,那是我们的五四运动,新文化革命,那是我们的悼念总理的天安门事件,
你什么时间开始有梦想的?你生命的梦想?那大概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吧,青春刚刚点燃,春天刚刚起步,风已经有些暖意的在耳边吹拂的时候,你渴望着,拼搏着,崇敬的夸父一样追索着。但不久,正如大多数的人一样,你的目光从星辰升起的地方,从瑰丽无比的地平线上,从温柔的黎明刚刚透亮的时候,渐渐内敛,为周围人事,为你所处的声音及各种举止相所纠缠,你的目光因此收敛,来听他人的骂声、斥责、肯定或者赞扬、嘱托或者吩咐,来看逼
前面不远是天坛政治和人事之间的斗争,让我感到厌恶,是一种恐惧吗?是小知识分子对世事变迁人生无常的恐惧吗?但我不愿意写什么政事人事,因为这种厌恶还来自另一个反应,那就是知道诸多事例及历史概况之后的一种情绪----耻辱和愤怒。原来,我厌恶的是那些耻辱和我不由的愤怒。我准备开始写的《恶邻》,就这样刚刚萌芽,便被自己除掉了------我就是要在自己的田地里铲除这些恶苗,植上我喜爱的花草,哪怕邻人又过来阻扰
神稚泉流飞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下午,因为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仲春周日的阳光,投入所居的楼窗,暖暖的明亮,映照对面的墙画,燃起大团大团暖黄色的火焰,寂静而柔和地燃烧。妻儿仿佛并无昨天旅游的劳累,呼朋引伴着,到三八节闹市上去了。其宅临街的楼下,传来诱人的小雨,隐隐约约。一个人在家可以做些什么,也可以什么也不做。那些工作和生活里的汹汹是非,那些同事和亲属间的蜗角纷扰,已外在我的清静世界。我躺在儿子的卧室
今晚,我们看月亮他的身影,在我的日记本中闪烁。四周岁的时候,我用腹部温暖他的一双小手,他冰凉而柔软的小手。那是我的罪过呀,摩托车速太快,没穿大衣,寒流越过摩托的前脸,收缩成锥形,正好袭击坐在踏板上他的背部,他娇小的背部。他说他手疼,我放慢车速,用腹部温暖他冰凉的小手。他的身影,在我的日记本里闪动。四周岁的那天。腊月十三的那个寒晨,我们走得匆忙,忘穿大衣,虽小心翼翼缓缓驶过冰地雪辙,却终于在半途中冻
下班之后,我去接你他们没有收场,而是坐在我的旁边,还有一人坐陪着两个孩子。男孩子额头正中的枪洞尚未冒血,那女孩子中弹的地方则不易察觉。我不相信他们真的会死掉,找到他们的睡铺前,看到空出的地方上,有血迹清扫过的理痕,新鲜而惊恐,便又有些相信了他们的死掉。之后,是我和一群亲属沿着故乡的铁道向西行进,耳边隐隐有车辆嗡嗡的声音,那种相信再次出现,因为前面浮现他们的棺木,他们小小的身体,难耐的收敛其里,而且
 手游《怪物猎人:旅人》微博账号开放:发文庆祝获得版号!
手游《怪物猎人:旅人》微博账号开放:发文庆祝获得版号!
 最强RS 6 Avant GT来了 限量66台正式开启预售
最强RS 6 Avant GT来了 限量66台正式开启预售
 说唱歌手&演员宝石老舅喝酒闹事被抓:释放后发博道歉 直言酒后失态爆撞路边无辜车辆
说唱歌手&演员宝石老舅喝酒闹事被抓:释放后发博道歉 直言酒后失态爆撞路边无辜车辆
 高速端到端 /AI 推理可视化上线 体验理想 V7.0 版本
高速端到端 /AI 推理可视化上线 体验理想 V7.0 版本
 索尼蜘蛛侠宇宙新片接连暴死!高管认为质量不差,还甩锅媒体
索尼蜘蛛侠宇宙新片接连暴死!高管认为质量不差,还甩锅媒体
 2025款腾势D9正式上市,售33.98万起,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2025款腾势D9正式上市,售33.98万起,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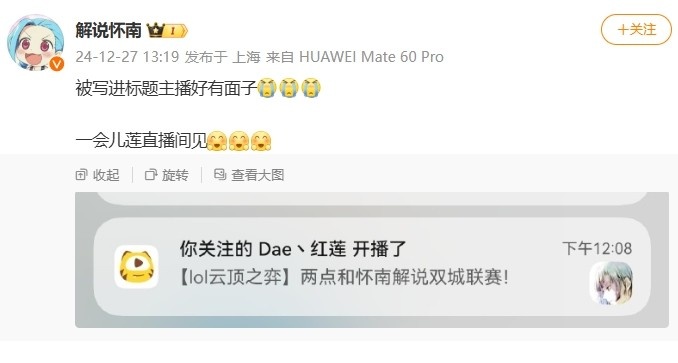 解说怀南:被写进(红莲)标题主播好有面子,一会儿莲直播间见
解说怀南:被写进(红莲)标题主播好有面子,一会儿莲直播间见
 朗逸NF/途昂PRO将于明年推出 奥迪A5L年初发布 AUDI新车年中上市
朗逸NF/途昂PRO将于明年推出 奥迪A5L年初发布 AUDI新车年中上市
 美国专业健身教练怒斥贾玲体重反弹:“秘密减重”搞的人尽皆知 全是围绕“减肥”的营销
美国专业健身教练怒斥贾玲体重反弹:“秘密减重”搞的人尽皆知 全是围绕“减肥”的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