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数字化情绪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是否可能也数字化?虽会因人而异,但一个时代一方地域内的情绪,窃以为,可以数字化数值化。我的经验体验,就我酒醉未醒------不是当日而是次日,是电解质受到扰乱或植物神经受到刺激的感觉来看,那些受伤后的创口,最敏感,数值界点最清晰。比如,可以感觉到植物神经在睡眠中,仍然兴奋着,半醒半梦状态中产生的幻觉,有难眠之时的图画记忆、阅读记忆,遇到奇山异川、神貌鬼状之地理时,
生死自如的睡眠不知道死,或者说不虑及感受到死,是不知道生的诸多意义,不知道生的快乐的。如何去体验死,来体验死?那沉沉的睡眠-----就是一日一次的死,尤其是无梦的彻底的睡眠。那深眠之后的苏醒,那死过之后的清醒,才会更深的体会到-----生-----原来如此快乐,如此美好。好多的人是没有真正睡眠的,不说当下中老年人流行的失眠,以及焦虑、抑郁等疾,即使简单的头痛多梦,便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在大规模的
载喜载悲,已望清明右边暖气面板的暖流声中,那窗外的另一个世界,不时传来汽车飞奔溅起的水声。今天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天气,我也在昨夜的醉态和今晨佩索阿先生的阅读之间,那仿佛是同样雨雪交加的世界里走动。我在反省,质问自己,曾经沉静的自己去了哪里?躲在何处?儿子没有出生之前,一场劫难之后,我从失去母亲的悲恸中走了出来,神灵又赐予我大地般的沉静,岩石般的孤独。闪电般与冥冥交往的日月里,我常常因为路边的一棵树,
我们的裤子大家非常关注服饰的流行,但可否关注它阶段性的变化?我也注视过它的历史,就其近几十年中的变迁,以写者的手力眼法,为您展开。文革时候的女人是不太穿裙子的,性别的差异与那个时代人性的相对模糊一样,少很多人注重男女性别的区分,不是不注重,而是田野里,天光下,女人也是半边天,风中雨中,一样的劳作,一样的自立。但是,窃以为,那时候的女性从根本上,从内心深处,依然是自守自保的,从长裤及上衫的偏开口偏开
狠心的家那心不是飞扬,是飘荡是游荡是散落,是混乱的飞絮,所以和对面的同事说啊,说弟弟的婚约,道当年那场风雪中,在寒冷的夜里,迫不得已走出家门,在外流浪。也许他们不以为然,还是宽大为怀,理解狠心的兄长?他们称为家的兄长?反正他们流浪习惯了,在那个叫做家乡的城市里,无家可归,和北方的其他城市里无家可归是一样的吧。那风雪里的灯,那除夕夜里的灯,可否迷障了我的爱弟我的手足的眼睛?那孤灯中的风雪,可否刮进我
打开的门进出我的家有三道门,像螺丝的进退,要么越进越窄,要么越进越宽,尖锐或者松开。进来要经过小区的门岗,白天少人,晚上则很麻烦,我们愿意所有进出的陌生人麻烦麻缠。每深夜归,人行的小门关闭着,被一张桌子坚固,要开自动的大门方可通行。小区不大,所以门卫熟识居住的人,特别是总会晚归的男人。进我们的楼道也有一道铁门,生人要通过铁门上的对讲机和房主通话,铁门才会“咔嚓”旋开,拉门而入。当然,亲友来访,总还
叫你作祟!精神聚集无旁骛,砥砺奋进是常态。神不守舍的时候也有,但没有今天的多,无论阳光如何绚烂,清晨的微风越过树林,在高岗上吹拂,心神总是不安。单位里的人事,久远的,附近的,纠缠不去,是祟进入而乱。久远的乱了人生,仿佛还要乱了前途及末路;附近的乱了心气,阴霾一样不散。祟在孽;孽而祟。早上的时候,还责怪妻子:“你怎么又送他上学!上一次我都没有吭声!娇生惯养的!”而其实是自己昨夜愤梦,儿子处处不听话,
清晨骄儿可谈心一个兄弟送了一个鱼缸,家人买来七条热带的鱼,其中一条斑马纹鱼,他个最小,但最霸道,总欺负黑红鱼中的一条。终于一天,他杀死了黑红,并吃掉了她的眼睛。喜欢动物的儿子见此情况,捞出斑马摔死,又下楼埋葬了那条被害的黑红。但我知道,儿子是善良的,自小就可以看到。最近,已经高中的儿子学业不汲,也许可以杀鱼葬鱼的事件,以他的正义感和扬善惩恶为契入点,和青春期的儿子谈谈心,以引导他更为勇毅顽强,从而
负心的左手或是一眼枯槁,或是满嘴酒气的他,是很少和我说话的。头晚饮酒已醉,次日那依旧亢奋的力量,还要寻找继续亢奋的地方,在小城里,在不三不四或者所谓的朋友圈子里,从上午十点开始,无论中午夜半,阴晴圆缺,灯红歌绿之酒肆,野店地摊之菜肴,哪里有酒精的热闹,何时可以激情,就到哪里燃烧。要么是在连醉数天之际,酒毒渐入脏器,流渗骨髓,在双膝及骨缝间纠缠淫浸,进入植物神经内扰乱捣乱;给他一记怕光怕声难以入眠的
悼念的梦幻列车-------纪念四大一因为是周末,好友们聚餐,昨晚睡得很好,过去不适的肝部和心脏,已不觉得异样,半夜偶醒,也是平安。朦胧中,妻子起床了,又听到她接电话的声音,大概是清晨七点多些。她过来了,她推门进来了,但是我约莫不平常,不好。果然她推醒我哭出声说:“旭,旭,四大老了。”我一下子坐了起来:“不要慌,怎么了,慢慢说。”(四大及四叔,家乡话)五十天前,妻子说,你们单位不是清明节放假吗,我
谁的羔羊与猫咪仲春的一天上午,到清虚街一家银行取钱,却在银行不大的门口,被几声叫喊惊扰。看到是六匹白羊,两两的,或歪斜的立着,或倒卧在地上;是受伤了的?还是已知道自己将要被屠宰的命?那叫声凄然哀婉,真的并非肉体受伤,概知自己的命运已绝吧。君子远厨房,是虚伪的仁义吗?吃素不就好了吗?而实际上,人们往往难以《把头埋在鸵鸟里》。那些倒悬在羊血摊上的一扇扇牲畜,以及肉案上被刀割的七零八落的碎块儿,总能使人
不求同年,但求同日傍晚的风,有时从南,有时从西,在朋友的店前,在我们的茶桌上缭绕,说已有大半年的时间吧,也没有向你们汇报“工作”。近段时间的事情,简而言之,其一就是送送朋友:同龄的人,不断的死;同龄人啊,四十多岁的人啊!不断的死。大家听了唏嘘。不仅唏嘘无关的晚风,也是唏嘘有关的西风东风。谁不死呢?死亡去之我们尚远吗?死亡的早,死亡的方式也如此进入视野。传说中,一个教学《五月的鲜花》的教师,突发脑溢
折叠的书语及岁月这是2013年12月17日的《光明日报》,半年前不知在何处,翻看到其间有《书林》之类的副刊,就拿了回来。今天站桩锻炼之后,关上办公室的房门,任同事们按照昨天会议的安排去静心工作,自己则在僻静处,找到这些文章阅读。此日报的些许版面是可收读的,《历史钩沉》中《胡适念的第一部书》,其父笔墨及题跋,铁花手书,不厚不柳而正道,略有飞笔之意,率性之许却总归周端;更有“湿乎庸言,勉乎庸行”的为人
儿子,我们去看雨儿子跑过来,伏在床上,问人是怎样睡着的。然后手舞足蹈,竟又干脆爬上来,骑在背上。我却想着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儿子艺术的情怀,保身的修养呢?他终于站起来,在我的脊背上站起来,奋力一跃,跳到床下。也许,儿子身体的茁壮,身体的长大和敏捷,是关于意识和性情哺育的内在和根本;也许,儿子今天的记忆,纵情及被呵护的记忆,是关于幸福和安宁得以认知的内在和根本。他又匍匐过来站上来,跳跃下去。床下不远
傍晚,音乐坐下来情调,风格,意境和气息有何不同?或者仅仅是视角的区别、感觉的区别?情调是情怀的格调,情绪的参差;风格是一种流韵,好像也是一种格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又兼备风韵的风尚的风气的格调;意境则指思想情怀可以综合自己的审美体系所要达到的某层地理,某种机体,只需要审视吧,也是整个作品蕴含的正在上升或者四处弥漫的神秘气息。傅雷先生,也许词穷,也许深知,一连串的把这些并不同类,游湖综合同类的概念,一
焦虑的傍晚一切都是亮的,不是说早晨的天光,而是晨光下的一切。那光在一簇簇树枝桠间透视而下,是无数的闪亮的光线,那一片片树叶,闪烁着旭日的光辉;并排停泊的车辆,发出金属耀眼的光泽。透过树林和车辆,透过成荫的百米广场,那铁篱之外的移动的炫目的光亮,也是一辆辆左右来去的小车。广场的开阔地上,赤光之中,一个耍练长鞭的人,也是闪亮的;随着他的旋转和猛然的转身,那身形成为巨大螺状的光弯,那鞭梢在摇甩之际的声响
焦裕禄的疼痛风从窗口缕缕而来的时候,我勾着头,知道此时是一尊菩萨。我的气焰,在四肢及头顶的百会穴之巅燃烧,耳畔尽管有焦裕禄的故事,周围是听会学习的同事,满满的,有所谓的领导;下午的政治学习,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我闭着眼睛,指令我的气焰,在涌泉、虎穴、牢宫、百会、人中之间,周流燃烧,盖有二十分钟之后。焦裕禄的肝部在疼痛,到贫寒的农家访问送暖。时隔多少年,焦裕禄的肝部一直在疼痛。焦裕禄,也是一尊菩萨
启蒙从十七岁开始平凡而幸福的少年,昂扬而志坚的青年,在那些简朴得有些野味,洁净得有些鲁直的年代,河岸的林木一样成长,以自然的阴阳顺性滋养。于我只在回顾那些年华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愚昧无知的同时,有着天庭一样豪光哺育的同龄者,高唱低吟着在我的左右,那些少年的他们,那些中年的他们,那些妙龄群策的风光,在我的身前闪烁,我却盲若不晓,触及不知。我的愚昧。这只是回忆中那模糊的印迹,真的美丽和明媚,早已忘记。因
文艺的婚礼我的心不能沉静,每每热跳。走到窗前,远眺西面群宅,那初秋的雨,滴湿的房顶和马路,不清的风,微摇着我脚下的桐叶,却想到,也许有人中午会邀请我,让我出门步行。我的心不能沉静,细汗在阴凉的空气中沁出,而风又从背后的窗门奔袭过来,浸出冷意。是我扁桃体发炎的缘故,是它红肿导致的焦躁,破坏我的宁静?我顶着冒起入眼的热涨,不时抹去鼻腔流下的清涕。《文艺的葬礼》的构思,不觉与鲁迅先生的《孤独者》相仿了,
华光普照悲情碧-------怀念母亲今天是母亲辞世的周年,二十多个年头了,风风雨雨。今天,旭日早已升起,在东方缓缓流动;踏着满目的明媚光,匆忙赶到许继集团的一个会场,这里的孩子在排练,几十所学校的孩子此处演练,为了六一节的汇演。会场上熙熙攘攘,到处是他们的笑声叫声,老师的指挥声。看看八点多些,唯恐打扰送过儿子已回家休息的妻子,便给北京的昱弟发去一个短信。其中被孩子们开始的演练打断:童稚的歌声,孩子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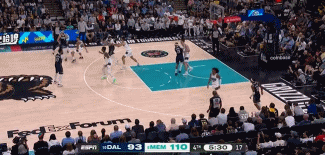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