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如此凄丽而美好若非才智的惊人,叙述难以行云流水纵情恣意;一般的叙述者,还是要讲求布局谋篇方式方法,以此技能来补拙吧。当然,讲方式方法也许依然是一种才智,尽管是叙述的一般才能,通过勤奋的学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但“拙劣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用尽膀臂、腰胯、腿脚甚至牙齿的力量,仿佛才可以,把这个可能是商品而非性灵的物件塑造出来,表达出来吧。一位知名作家,很少抛头露面的作家,在凝视京城和外域及远
宁玥居处玥居宁“我不止一次梦见,默默无言的妻子和人私奔,或与陌生的男人另有隐情。她总是麻木着面孔,冷漠着一切一样,或者这个世界欠她什么,还不尽的仇怨。这样她在不算少的家居和未知何处的空间里,她与人私奔,与陌生的男人在一起。为此痛苦不堪,梦中哭醒。”弗洛伊德解释说,这是人潜意识愿望的达成,不是你希望出现在梦中的那些剧情类的结局,而是经过伪装的另一个愿望的达成,即你害怕你的妻子外遇,尤其情感上的依靠成
春花三弄一并无太多繁丽的色泽,一场微微呼吸似的风里,夹些尘埃;满地悄无声息似的草间,散着杂花。这是现实的早春的午后,一副慵懒的模样,处处一派的质朴与平和。这些时候,我会骑上车子,踏到门口,为车子填气,踏回井台,为车架净面,也许在质朴平和的氛围里,为我的家人,做一些有益的事儿。我是大可不必踏车上班的,但我唯有如此,才使我再次体验生活的平凡和日子的质朴本色。起先我未意识到这种色泽,而傅雷先生的一番言谈
看她,冰心玉洁的诗人她的文字和情怀渗入生活中繁复的绿荫中,风烈烈;渗进默默的交谈里,乐声声;暗无声息的闪耀着的星光中,明明灭灭。她的大海,她的岸线,夜的灯光,季的鲜花,交织着,融汇着,在她和她的世界,溶溶的静静的涌流;涌流一生一世。而凡俗若我之人,除非在工作余暇的雪后,或雨歇,恰有傍晚风临,悄无友人造访来电,也许,这样的光阴中,才可以勉强做了道场,行了沐浴了吧。也或者刚刚一场劫难,大病初愈,至少是
无法安顿的风中原腹地的城市,古称颍阳的许昌,城西五一路南段,两捅巨大的烟囱,依然不顾环保,在无风的初春,直直冒烟,灰白色的烟柱,有些“孤烟直”的畅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是所到的院落,哪有长河?处处只有低矮的楼群,懒懒散散的,灰色的暗红的,零落在笔直烟囱的四周,没有犬吠,没有鸡鸣,不是村落,却是人间,间或传来几句的人话,知道这块地域有人存在,有人活动。这些零零碎碎的人语,从那些破旧的蒙尘积诟
港澳回归祭题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闻国共就抗战中流砥柱的问题存在异议,尤其是对岸的另些旧相识,那样的态度,不由唏嘘。谁为一己之利?半梦半醒之间,依稀香港的初闻,是一种称为香港衫的T桖。八十年代后期,中原如许昌者,谁知道T桖是什么意思呢?T桖是什么名词呢?但“香港”开始在草根民间市井间微风。那种T桖料薄色艳,且装饰胸链,是那初夏的风光中前所未有的时尚。再有就是港片了,李小龙,黄飞鸿,王家卫,等等等等
春光中的新坟-----《颤栗幼林》序明媚的阳光从东方普照大地,刚刚出土的林苗一车车的载去,余下新翻的泥土和鲜活的土坑,泛着最远古最神秘最有力的气息。麦苗更绿了,远眺舒畅适宜;高高花坛里的白玉兰,就要在不久的一个早晨开放,那白白的洁玉而含着嫩黄的美色,仿佛已盛开在楼下;有人着了春装,潇洒的在楼道上走动,眉宇间洋溢着青春的情与力。而夜晚的辗转不眠,又是怎样深揪着我的灵魂,那突兀的新坟不断在半梦半醒中凸
长篇纪实散文:水啊,向西流-----许昌抗战周年祭一阅江山之雄秀兮根叶之幽情举望族之大泽兮风雅之勃兴二夜,一如既往地安宁,像旧林中的宿鸟,故渊中的老鳞,像雨声中的眠音和睡梦中的微笑。一切都被温柔的沉寂和鲜花的棉被覆盖着。还有大地和房屋的微息,还有无边际的漫布全镇的隐隐口渴。漫漫的大山沉睡着,无日无月,黎明前更如黑暗而沉寂。千万年来,光,常常散淡地梦幻地洒在他庞大的躯体上,与草木禽兽密语。近百年来,
新居遐思一我双腿疲累,觉得沉重,却仍然抑制不住安家的自足和愉悦,无论如何,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方空间,那些仍然杂乱的家物,却样样充满深情,那脏兮兮的柜子锅碗,仿佛终有了归所,安静的不卑不亢的展开。上班的路上,宁静飘着的雪花,如此清爽而平安。平平安安,这平凡而有深意的词语,如此温暖而智慧。平平安安,奢论荣华富贵。站在学校二楼的凉台,那雪花已经开始飞舞,微笑着飞扬,相信上午所发生的一切,
自我雄风与雌风中原腹地的城市,古称颍阳的许昌,城西五一路南段,两桶巨大的烟囱,依然不顾环保,在无风的初春,直直冒烟。灰白色的烟柱,有些孤烟直的畅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是所到的院落,哪有长河?处处只有低矮的楼群,懒懒散散的,灰色的暗红的,零落在笔直烟囱的四周,没有犬吠,没有鸡鸣,不是村落,却是人间,间或传来几句的人话,知道这块地域有人存在,有人活动。这些零零碎碎的人语,从那些破旧的蒙尘积诟的
不定的风,根固的树那几天里,只有搬家的匆忙,无暇顾及原来院落的情景。关于生活了近二十年的院落,那里的一言一行一老一同龄的院落,三楼陋室对窗那颗巨大的梧桐,小学院内那一棵又一棵粗大的杨树,一草一木并不关情?那些时候,院子里的老人一个又一个相继离开;我的母亲也是在那时离开了我们-----哪怕在我的梦境深处,我与母亲相约从未离开。而终将,我也要离开那里,到另外的院子里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母亲过世,自己孤
上海,一座新的烽火台好像现在的状态,才是正常的状态,因为这是从家乡到朋友又到亲属处的旅途,也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巨大的单元不断寻找进步的写真。村庄一个一个不说,城市,大大小小的城市像村庄一样,一个又一个展示在我们的两侧;还有光阴,那晃动的又勇往直前的时光车轮滚滚滚滚车轮。尽管车厢内部,那么多既熟识又陌生的人们,在走道寂然无语,来来去去;在座椅上,近在咫尺,彼此相安无事。我们从中原出发,用不了多久,就要
站稳你的脚跟脚跟处的骨头最清醒自己在什么地方,走着什么样的路径,他仿佛一边是受着奴役,忠诚的受人的意志和愿望驱使,一边又常常嘲笑他的主人:因为他被昂首带动,步阔脚稳、仿佛沉静而有行进着的时候,也许狂躁的雨季及萧杀一切翠绿的寒秋正缓缓到来。有时候,他又蹒跚的像一个老人,在狂热和眩晕中,在不甚明亮的夜色里,有些轻浮的搭车,迷离着岁月和目光,在微明的灯下回家,入门踉跄;常常遗物在租车里,甚至信手扔掉注视
地狱之门这绝不是一部电影,但他的确生还。几个人一道乘车,走过一道垒有墙的河堤,堤坡草皮绒绒,堤下河水微亮。他清晰的记得,遇到一个铁道口时,路径向北分叉,又走了好远,穿村庄大道,过散户人家,一直不再折弯。但是,暮色笼罩,无风画惆怅。他向前走去,他执着而沉稳的将到共约的地点时,也许他走的过快,忽然间,他发现,同行者已全部消散,好像那个世界上,向来只己一人向目的地前行。他醒悟之后,孤独的站来一会儿,清晰
同事老黄恍惚还在昨天,却又知道不是。背靠椅子默默算来,那应是1999年的冬天,距今已是十几年半的光景,他,我们的老黄,离开了人世。当时,他正值四十多岁的壮年。老黄同志是个农村教师,即使从农村中学调到郊区中学,浑身仍然散发着浓浓的土气。他身体矮瘦,隆鼻炯目,皓齿乱髭,皮肤暗黄,笑意盈盈,却不修边幅,一套蓝色中山装,色泽不正,也谈不上干净,皮鞋好像常常在菜园中劳作踏归,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不变的样子。即
立秋的烦恼晚来洗漱,抬眼望到西窗之外的许继大道上,一辆白色的车子缓缓驶来,是110?,近来仔细看去,是110。今日这样的时代和街头,如若违反了什么规矩,比如有人忘了什么证件或者产生误会之时,有人就对威严的警察说:昨天立秋,昨晚可够凉快的,呵?你猜警察会怎么回答?他当然横眉冷对,还会嘲讽你立什么秋,快拿证件,快交罚款,与立秋有什么相关?“干你的活去,说什么立秋”。如果夏日炎炎的傍晚,专门从脚手架上下
拉幕人的孩子拉幕人正在不知何处的方位,向幕前奔行,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只是四起的脚步声,有些杂乱,或者被另外的各种杂音掩蔽着,戏谑着。那些杂乱的声音,是孩子们放学排队出门的哨声,一二一,一二一二一二一;终于走出学校校门,不多远,孩子们散队之后的欢呼;还有家长接儿唤儿声在滚滚车轮中起伏。拥挤的孩子们家长们,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傍边是一个父亲批评女儿写作业的声音,带着地方味道极浓的普通话,女儿刚刚吹起
雪在燃烧我一笑暗淡的室光,再有迷离的醉眼,要你挥墨书情,你会有什么样的志趣?写下什么文字?境遇相异,遭遇不同,怎么可能会有相接或相近的墨意心声呢?会有的,总会有的,比如根本的生死,常态的喜怒。对我而言,如今想要谈的是在世处事为人的某种态度吧。一位暴走江湖、恩怨至生死边界,在我们的城市赫赫有名的江湖中人,其超凡出手之事,恨极凶悍之为,不畏一切力量之胆,游离于苦厄追捕之识,都是让自己敬佩的,是一部传奇
有谁可以安慰我无论惊心动魄的毒品吸食传闻,还是雨夜为爱情自残的各类表演,种种异像,好像都无法感动我尘垢厚积的灵魂,只有她才可以回到我的心怀,让我安静?让我情平吗?只有酒精和非常的类似异性的情感才能让我兴奋,让苦涩的情怀生长夏夜里的林木?我寻找着久违的情怀,寻找字如玑珠的灵感,比如苏轼的《三槐堂记》、“赤壁两赋”,还有柳宗元的“永州两记”,都只与眼神相遇,与耳党为邻,并不走进内心,并不被内心所挽留吸
居于高尚之寓的龙世昌初夏之季,这是新的办公室,暂居于此工作;寄居于斯之感,只是觉到尺寸之短,如若人居于世是一丈距离的话。夏风微抚,寄居于斯,是说从原来的工作场地,借调到这里,别人临时给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相对于自己更久些的工作,此借调仅此尺寸的空间。当然,另一重意思的把握,是说人的一生也是寄居,也是借调到另外的领域内工作生活,如果也能把握的话。如此如此,与时相融再无寄意的境地就接近了。因为对于一个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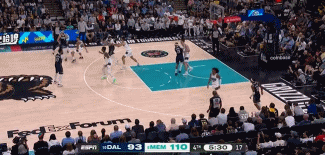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