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的金钱观发生的特别早,他不像二哥那样小打小闹,干就干大的,虽然也不放过别人碗里的一粒米。大哥最早的爱好是照相,朋友家有有照相机的,是那种双镜头挂在脖子上向下看的120照相机。那年代,脖子上挂一台照相机别提多有面子了,取景,对光圈,调焦距,按快门,带自拍。后来就超常规跳跃式迅速发展到能自己进行后期制作的水平了。把照好的底片在照相馆冲好以后,买了显影粉,定影粉和相纸。回家后把闲人劝出去,换上红灯泡
铜是不太容易生锈的,而铜锈的颜色很特别,它蓝中带绿,绿中发蓝。据说铜还有一种臭味,我没有注意过。二哥是能打架的好手经常替我上前,还是“鬼点子”特别多的人,他是小孩子群中的头,跟着他有底气,有好处,有面子。他也是经常在外惹事的人,三天两头就有大人领着哭泣的孩子来找,母亲就成天给人家赔不是道歉,因此母亲叫二哥为“惹事布袋”。他还是从小就知道钱有用的人。记得有一次过年走亲戚,每年舅老爷都是先给压岁钱,一
两个哥哥的金钱富贵梦比我早了三十多年,从小我就跟着他们挣钱我当帮手,却没有学会挣钱的门道。惊蛰过后,入夏时节。柳絮也飘舞了,花儿也兴奋了,墙头的甜酒花也熟了,地生的虫儿强壮了以后也想恩爱了,两个哥哥也早准备好了手电筒和小铁桶想挣钱了。晚饭后我们哥仨出门很快,母亲知道我们有行动就不用洗碗了,父亲也知道我们有行动就不用练武了。两位哥哥一人一只手电筒我则提着小铁桶,他俩在前面手电筒探路沿着墙边弯腰低头仔
遥想当年,除了吃点好的很高兴外,电影就是另外一个大大的乐趣。灯光球场:我们城东南方向是工人俱乐部,记得那时只有工人俱乐部,不像现在啥俱乐部都有就是没有了工人俱乐部。紧靠俱乐部有一名曰“灯光球场”的体育场馆,这个“灯光”就是一个没有顶棚的露天体育场,周围是看台,体育场中央上空有很多大灯泡,夜晚来临,灯一开,灯火通明,但不一会儿成片的飞虫也向光明飞扑而来。这是一个多功能体育场,没有友好比赛的时候就放露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与莲莲在寒假里追逐着嬉笑着数南飞在蓝天白云上的大雁了忘记有多少次了我与莲莲在热浪翻滚的田野里背着她一起数收获的历史了根本就没在意莲莲如桃的面如桃的眼如桃的唇如桃花遇春风的秀发或许已经忘记在池塘边在小河旁讲着只有莲莲害怕的故事了又一年暑假又回老家一路听着知了的海豚音我唱着少年的歌谣就回到了熟悉又向往的老家不仅是老家是故乡不只有爷爷有奶奶还有我魂牵梦萦的莲莲和影印在花花草草上莲莲的影
大哥手很巧差一点就成了木匠,或许邻居家有一个是木匠经常过去看的原因,或许是父亲教了一个是木匠的徒弟,也或许是木匠有一门会挣钱的手艺又会做家具因此人就能干就好找对象的原因···家是老房子,前边有窗户而后边是上窗,是大哥独立自主自立更生前无家人后无跟随地进行了改造和美化。记得他买了大刨子,二刨子,净刨子,开边槽的刨子,推圆边的刨子。还有大小锯和线锯,凿,铲,斧,锤,锛,锉等木匠常用工具,首先自己做了一
大哥是家里“新奇特”事物创造者,当我还满足于大茶缸子喝水急了就喝凉水的时候,他不知如何从哪里弄来一个透明的大肚子玻璃说是可以冷水的壶。这个“水壶”像是一个军用旅行水壶,但没有带子就不能背在身上。而且它的肚子是圆的,上部分一下子收起来像个坛子,其颈部却比坛子的长很多,用手握上去很舒服。平时早把开水装在壶里冷着,再扣上一个原配置的玻璃杯子,一是防尘,二是喝水不用再另拿杯子。壶里的凉白开清澈透明,拿起来
突然有一天,大哥弄来十几件衣服。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就算过年兄弟三人也不过每人两件新衣。开始还捂着盖着,闭上门,不吱声,你也挑我也捡,三翻两翻,三挑两捡,料子很好,毛呢的,纯毛的,咖啡色的,翻领的,大翻领的,夹克的,花格的,连体衣裤,有腰带的大衣,挑来挑去,都挑着合适的了,没有我的,挑不到合适的,我都快急哭了,哪一件也不合适,就看中一条围巾,大哥还不给我。那条围巾:毛麻的,薄薄的,两头散,三色绿
哥是家里物质文明的爱好者,追求者,和实践者,而且很疯狂。家贫未必出孝子,但一定能出改革家。狗不嫌家贫是因为狗不知贫富和可怜的忠诚本性所致。大哥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可以先摸着家里的东西练手,等有了资本就独立或是出国吗。有线广播的线路到街上了,早午晚有时能听到“潍坊人民王八蛋”(不标准的普通话加上不仔细听就把“广播站”演绎成“王八蛋”了)现在开始广播了。这是多么神奇的声音,大哥是如何接到自己家里的,还接
早先养个麻雀,养个金鱼,养个蟋蟀,养个蝈蝈,这叫“耍物”。养狗养猫有任务,狗负责看门猫负责捉鼠。养鸡养鹅就会有物质上的享受,如果知道那只鸡今天要下蛋,会高兴一整天。记得我们家曾经养过一只乌龟。他来我们家时已经拳头大了,这龟先生天生一副老者模样,没有白头发,没有长胡须,一双芝麻大的小眼睛经常定睛神视。他经常两腿蜷起双臂一缩静观我家一场场战争风云起,又重归合家欢。一幕幕人间悲欢离合剧,一丝丝前生吉凶祸
我生长在风筝的故乡,当然对风筝略知一二,比如早先放风筝不叫放风筝,而是叫放“鹞子”。放了寒假,回了老家,眼看着一场一场大雪攒在农田里,攒在墙头上,攒在房顶上,攒在被寒风冻僵了的枝枝杈杈的树冠末梢,攒在麻雀叽叽喳喳到处讨饭的回声里的时候,老家的乡亲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自在的时节。早睡晚起,每日两餐。平静的早晨,安详的夜晚。男人晒太阳,女人纳鞋底。白天老婆孩子团在热炕头上说笑打闹,听见狗叫就捅破窗户纸一
差不多每周六,周日都要回老家去看爷爷奶奶,开始是跟着哥去,后来也独自去。特别是年根放了寒假,去的就更勤一些,来回捎个话,来回发个“快件”,都是我的活。我回到老家不是快中午就是快黑天了,多是放下东西就马上去找莲莲玩,莲莲多是吃完饭再来找我。一次奶奶做的粥,是放了姜末,葱花,豆腐干,咸盐,粉条还有豆的那种,我硬是治着莲莲喝了大半碗。第二天上午,我挎着筐子,筐子里的东西上面蒙一条毛巾,往回走。年根了,进
写这个话题很别扭,很纠结,很小气。班里的班长对我说:他想买两张电影票去看场电影,问我有没有一毛钱。我马上拿出一个五分,一个二分,三个一分的硬币来给他。他说下周还我,我就信了。当年的学生电影票五分钱一张,你说有多便宜。下周到了,我没有故意去看他。他没有还贷。下下周又到了,我故意过去看他,故意叫他一起去上学,故意与他一起放学,他还是没还贷。一个月了,我发现他没有还贷的意思,我离他远了许多,放学时又高喊
小学时期经常开一开全校师生“忆苦思甜”大会,会后还要一起吃“忆苦饭”。“忆苦思甜”大会的指导思想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喝着甜水长大的一代。因此,不能忘本。更不能让一切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团结过去。其实,“忆苦思甜”大会与现在的追悼会有点相似,其悲愤,呐喊,抽泣声还有过之。在我们片区居委会有一位女主任是远近闻名的“血泪”控诉大王。想起那万恶的旧社会,她能声泪俱下地
新手上路自从那夜独自偷学了骑自行以后,我就以会骑自行车自居了。看到有新人学骑自行车还在外围指导,并大讲如何大胆如何技巧等要领,还悄悄告知在后面扶车的人如何在骑车人不知情的时候放开手。这可好,本来骑车人骑的好好的,但发现扶车人不扶车了,一个惊吓自己摔倒在地。我就没事似地跑开了。虽然再没有机会练习过骑车,但总感觉自己能骑很远。终于来了个机会,周日说好要独自去父亲的单位里洗澡,我央求着还要骑着自行车去并
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居委会要安排片区的居民夜里值班,家里多是安排一个闲人去,是猫就避鼠,这是一份很光荣的工作,“地富反坏右”之家的闲人还没有这资格呢。因此,“义工”不新鲜。当年居民区的夜晚除了街上几盏路灯和偶尔天上的星星闪烁外没有一点儿亮光。没有光污染,没有夜生活,没有夜经济,没有多余的电去浪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是稳定的和谐的互尊互让的没有剥削和掠夺的正常关系。我独自坐在路灯下
父亲的师傅是我们当地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是五行“太祖功”的代表人物。父亲是大徒弟,一生习武,演武,教武。虽没有真与人打过架,动过武,但也算是当地好手,也算桃熟李肥。在没有金庸,梁羽生的年代。在三国,水浒,杨家将的年代。在不搞经济,没有电视的年代。所有人的空闲时间很多,除了工作吃饭时间大家都在修身养性,养生是一种淡然的自觉的行为,绝不是如现在这样的全民恐惧被动还破财又不知所云的欺骗运动。俗话说:冬练三
无忧的童年快乐的小学时代,没有翅膀也能飞没有梦想也做梦没有压力也能高。但有些事记忆深刻,有些事奇奇怪怪地发生了却又想不明白,还没明白呢还想着呢。冬天的课间十分钟,同学们除了踢毽子,跳绳,“猴子抻着猴子跳”外还有一种省钱又暖和的游戏想来特别有意思:找一个墙角,全班有一半多的同学哄跑过去,男多女少,女同学都是高大威猛的。开始大家乱乱的挤在墙角处,一会儿就自然地顺墙边横排成一队用力向墙角挤去,你挤我也挤
初夏时节,父亲领我们哥仨去理了个发。从家里出门上街向东不用二百米是小十字口,这可是热闹的地方。向南不远有文工团,向北路西是三食堂,油条豆浆不常吃,肉火烧多用来解馋,别说下馆子了,只听说两块钱就能请七八个人大吃一顿。三食堂的对面是“上海理发馆”,隔壁是“东方红”照相馆。再向北是大十字口,有医院和土产,菜组和银行。理发馆有一男一女两位师傅,我们去时恰巧没顾客。父子四人两两轮流坐下,脖子上围一圈毛巾,肩
吃饭是个大问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本人就是个吃啥啥不剩的主。十一二岁的男孩正是装饭的时候,何况是兄弟三个,因此,做饭也就成了大问题。每到饭点,全家人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做饭有分工,吃饭有规矩,这是不能乱套的,若有好事者想改革一下,就会有一番大争论。记得有一次中午吃饭,年龄最小的我如往常一样摆好桌子放好板凳就坐在饭桌前老实地等着,看见母亲拿好了筷子,看见母亲拿好了菜盘,看见母亲拿好了饭蓝,看见母亲舀
 Oner:没想太多,单纯想留在T1;长久效力于一支队伍是目标
Oner:没想太多,单纯想留在T1;长久效力于一支队伍是目标
 kid感谢王思聪,在IG打2年等于做十几年直播:退役那年校长给80万
kid感谢王思聪,在IG打2年等于做十几年直播:退役那年校长给80万
 能晋级S赛吗?DK更新2025选手合影照
能晋级S赛吗?DK更新2025选手合影照
 宁看节奏酒桶对战Doinb,五个刀漏四个 水晶哥语音鼓励补刀没用
宁看节奏酒桶对战Doinb,五个刀漏四个 水晶哥语音鼓励补刀没用
 王者荣耀公布明年赛事日历:世界杯、洲际邀请赛S3、冠军邀请赛!
王者荣耀公布明年赛事日历:世界杯、洲际邀请赛S3、冠军邀请赛!
 经纪公司:对T1 Coo与Zeus现场协商并不知情,Zeus迅速决定转会不是事实
经纪公司:对T1 Coo与Zeus现场协商并不知情,Zeus迅速决定转会不是事实
 XLB:如果Doinb因为我那句话爆了 我为此道歉 那很明显开玩笑的
XLB:如果Doinb因为我那句话爆了 我为此道歉 那很明显开玩笑的
 冯骥称《黑神话:悟空》年底有惊喜 外媒猜想:会有竞技场模式?
冯骥称《黑神话:悟空》年底有惊喜 外媒猜想:会有竞技场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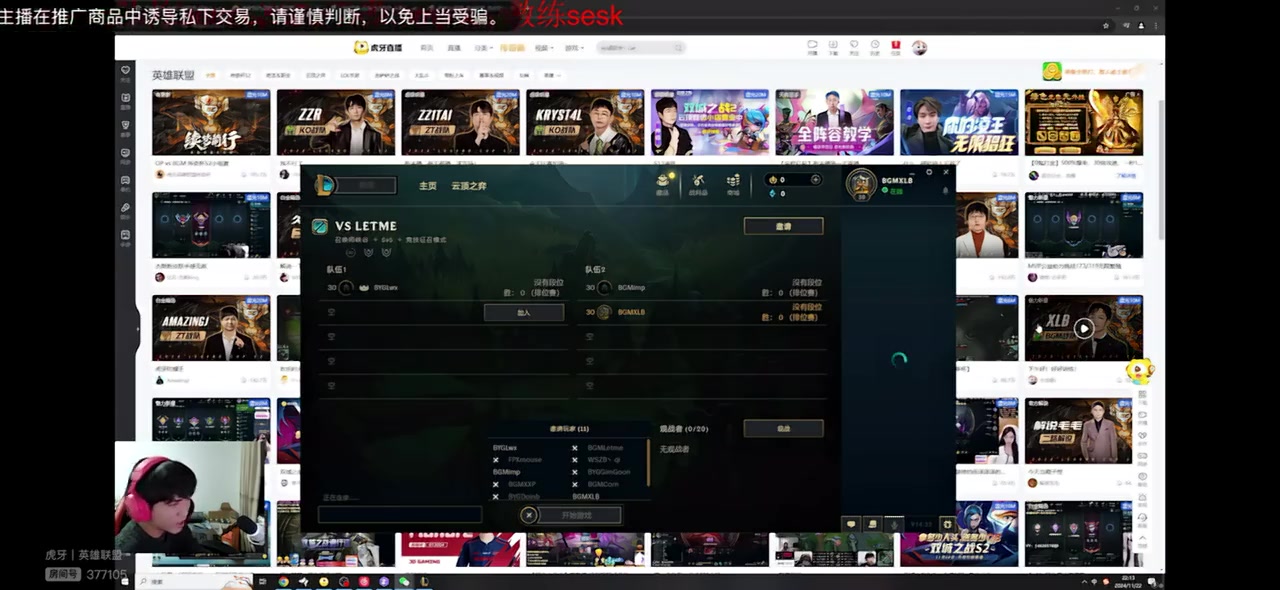 XLB:打都没打你怎么知道我要搞本?来宠粉模式,抽个奖吧
XLB:打都没打你怎么知道我要搞本?来宠粉模式,抽个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