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爱心播撒种子谁就会在秋后收获光荣
老舍茶馆的老板不是老舍而是一个叫尹盛喜的后生老舍没干过老板这行当只是教教书写写文章什么的但后来他就写出了名尤其是《茶馆》尹盛喜这后生现在吃的不是老舍就是《茶馆》即使老舍拿着《茶馆》当地图也别想找到昔日那家茶馆了
月满西窗独入梦乡徜徉白山镇已不是想象中的模样想当年欢歌笑语精神变食粮忆往昔挥汗如雨天堑变天堂几代人用青春和智慧把山沟沟托成了金太阳喜鹊飞来筑巢斑鸠跑来啄梁花香鸟语依旧而泪水落满母亲的衣裳爷爷化作了春泥父亲站成了胡杨我辈散落成蒲公英的种子四处飘荡故乡故乡睡梦中最深沉的忧伤
枣园灯光蘸满枣园的灯光和抗日的烽烟毛泽东用如椽巨笔挥就了《论持久战》和《论联合政府》在洛川和瓦窑堡的窑洞里拧出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和新四军用小米加步枪催生了一个嗷嗷待哺的新中国东北抗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爹娘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他们用庄稼汉粗砺的手指叩响了复仇的扳机天当房雪当床树皮棉絮当干粮黑土地上的汉子们啊腰杆子宁断不屈八女投江八个美丽的女战士用生命书写了自己的圣洁当硝烟散尽牡丹江
春雨四月的一场透雨浇开了母亲锁紧的日子她的倦容里开出了满院子的雪梨花母亲牵着我童年的记忆兴高采烈地走向了田野父亲吆喝着耕牛犁开了山梁上的泥香母亲把一粒粒金种子播撒出神奇的诗行泥燕故乡灰色的屋顶站立着一注注挺拔的炊烟和一抹像烟幕一样杂乱的翠绿屋檐下的泥燕成了母亲的新邻居它们来回翻飞衔来了一串串泥土气息的春光母亲仰起脸看乳燕叽叽喳喳地歌唱从春天看到了秋天从青年看到了暮年把自己满腔的柔情塞满檐下的一个个
既然既然鸟儿的理想属于天空当翅膀坚硬起来的时候它毕竟是要飞起来的
家乡是梦里的一方沃野生长的全是思念和乡愁站在繁华都市的窗口我渴望一场淋漓的秋雨焦躁不安的人们在疯狂谈论股市涨跌和邻里绯闻他们看不见我的家乡那漫山遍野的大豆和苞谷高楼林立如森林却听不见布谷鸟的叫声道路深切如血脉却听不见溪水的流淌声街道上人声鼎沸却听不见母亲呼唤我的乳名自从母亲用皲裂的双手把我从仄斜的房顶上放飞我就被岁月的犁铧翻来翻去摸着下巴上花白的胡子我才慢慢醒悟故乡才是我生命的热土
我已经习惯了寒冷的冬天我不清楚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苍蝇在冬天里上下翻飞从苍蝇们的口气里我明显感觉到冬天的寒意它们到处追腥逐臭在公园里在路边在餐桌旁在我的烟雾里苍蝇们不懂得爱护美丽家园他们的翅膀煽动起的深渊足够断送我的理想和信仰我举目四望发现唯有脚下的土地是坚实的而脚下的路有千万条因此我习惯了歧途
‍老水牛的血泪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题记我是一头非常普通的老水牛,名字叫沙牯。这是主人给我起的名字,我小时候妈妈没有给我起什么名字;爸爸也没有给我起名字,我甚至不知道爸爸是谁。沙牯听起来像是个母牛名儿,是的,我就是一头老母牛。公牛一般叫牤子、黄犍之类的名字。众所周知,我们水牛家族跟驴、马、骡子等兄弟们一起,祖祖辈辈发扬艰苦朴素、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
第一章抄袭之作这一天,大概是晚上——因为晚上是我最无聊的时候。无聊?对!在这个嘈杂喧嚣、污染严重的都市,会有多少人感觉到有聊呢?“聊”是什么东西?我搞不清楚。但我对“有”和“无”倒是多少了解一点,那是老子和庄子研究的哲学理论。不瞒你们说,我有聊的时候确实很少,除非喝酒,因为喝酒能够麻醉我的神经。实话告诉你们吧,反正我的时间多得无法打发。妻子李海青已经抢占了电视机,目前正坐在沙发上出神地看着一部像嚼
小说终于写完了,我的心里却陡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慌。李海青也替我担惊受怕起来。这篇小说就像我们心中的一团火,如果不立即把这团“火”从微机里输出来,寄出去,心里好像随时都会爆炸。或者说,那台微机就是我们家里的定时炸弹,马上就有可能爆炸!我和李海青马上手忙脚乱地把它输出来,打出租车去了邮局,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将它顺利地打发走了。虽然心中像一块石头“咣当”一声落了地,但仍然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无法预料它的前途
说句实在话(我保证,再说最后一句),李存葆大哥的成名作——《高山下的花环》我是在家乡念初中的时候流着眼泪一口气读完的,相信他在看我这篇小说的时候,应该伴随着山东人那种豪放的朗朗大笑吧。我俩的这两部小说,一笑一哭,很是幽默,也很有戏剧色彩。是笑好还是哭好?我说不明白——其实我心里再明白不过了,但我就是不说。我很会做人,是吧?如果说明白了,就显得太不谦虚了。因为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中国人历来
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部中篇小说《葬》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在《葬》中我想反映这么一个文学主题:就是“逃跑”,或者叫“出城”。说句真心话,因为生活所迫,我现在的工作非常尴尬,干的是一种给领导写讲话稿的职业,就是一种给别人做嫁衣的无聊透顶的工作。你们说,我写出来的讲话稿,里面全是我个人的观点,为什么非得让另外一个人(领导)代替我念呢?难道他们念得比我好吗?这个问题非常荒唐,非常尴尬,但大家却觉得理应如此。
跟朱文通完电话,我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虽然自己比朱文小两岁,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还是把我远远地拉下了。我摸摸下巴上的胡子,自己悔恨不已:都四十多岁的人了,黄土都埋到半截腰了,怎么还没有点儿正事儿呢!“老朽已知光阴迫,不须扬鞭自奋蹄”,于是我自吟一首现代诗——《顿悟》,逼迫自己奋起直追。那天我坐在大河边垂钓看见一大群风风火火的人在河里摸鱼好大好大的鱼被他们扔上岸磷光闪闪照耀着我的双眼我已分不清那深
自己若真能得一项诺贝尔幽默奖,那自然是一件美事儿。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朱文兄,听说你前些日子骂诺贝尔文学奖是狗屎,有这么回事吗?”我在电话中问他。“没有,没有,我骂的是××文学奖。”“你骂得好,骂得地道,骂出了一股酸溜溜的醋味儿。——就像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猴子。我觉得你很有种,简直像我一样有种(但我的胆子比他小,我应该承认,这点儿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但说到骂茅盾文学奖,就是打死我,我
说句实在话,我非常钦佩王小波。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写作,在用自己的良心说话。他能非常高明地“从毫无诗意的世界中找出诗意,从悲剧现实中提炼出喜剧性,从合理性世界中挖掘出荒诞性。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寻找神奇和有趣。”我的岳父突然死了,这应该说是一个悲剧性事件吧,但我横看竖看,上看下看,怎么也没有发现其中的诗意和喜剧色彩,难道是我的眼光有问题?我揉揉眼睛,再看,还是没有看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于是
说实在话,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文学家。虽然现在的文学家的地位已经远不如原先那么显赫,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无文学巨人的年代,虽然文学家的收入已经低于别的职业,虽然现在的文化市场非常混乱,虽然……但我还是非常想当一名文学家!文学家的起步是很难的,不像余华说了句“这工作倒挺适合于我”就会马上成名的。作家新秀毕飞宇1987至1991年,他一直是在写了退、退了写的过程中拼出来的。他说,“无休止的失败激励了我的
这一天,大概是晚上——因为晚上是我最无聊的时候。无聊?对!现在谁还有聊呢?“聊”是什么东西?我搞不清楚。对“有”和“无”我倒多少了解一点,那是老子和庄子研究的哲学问题。不瞒你们说,我有聊的时候确实很少,除非喝酒,因为喝酒能够麻醉我的神经。实话告诉你们吧,反正我的时间多得无法打发。妻子李海青已经抢占了电视机,目前正坐在沙发上出神地看着一部像嚼过了的泡泡糖一样味道绵长的肥皂剧;儿子小威已经占领了写字台
当村姑那对倔强的羊角辫儿温驯驯地耷拉成沉甸甸的谷穗儿村姑便在那个金黄色的季节成熟了成熟了的村姑将那对温驯驯的辫子从胸前甩到背后从背后甩到胸前甩得爹娘不敢打她的屁股了甩得奶奶不敢喊她的乳名了村姑那对甩来甩去的大辫子把村里小伙子们的梦想都甩直了他们躲在草垛后或树林里把村姑的乳名唱成山歌村姑的脸蛋儿却羞得像树枝上的红酸枣扭身关上了自家的房门后来后来是镇上农科站的大学生用知识和红瓦房将村姑的娇羞关进了吉普
单位要召开工会会员大会了。起草工会工作报告的责任自然落在了秘书小王的头上。她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各部门领导,熬了好几个通宵,终于把报告的初稿拿了出来。小王把稿子拿给单位的各位领导传阅,征求修改意见。单位领导不算太多,总共二十位:厂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七位副厂长,再加上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五位厂长助理,还有行政和党委办公室主任也要过目……等稿子传回小王手上,时间
 纪录片《眼见为实》 圣枪哥一步之遥的遗憾
纪录片《眼见为实》 圣枪哥一步之遥的遗憾
 前LPL英文解说Kitty晒上海Major现场照:被导播拍到啦!!!
前LPL英文解说Kitty晒上海Major现场照:被导播拍到啦!!!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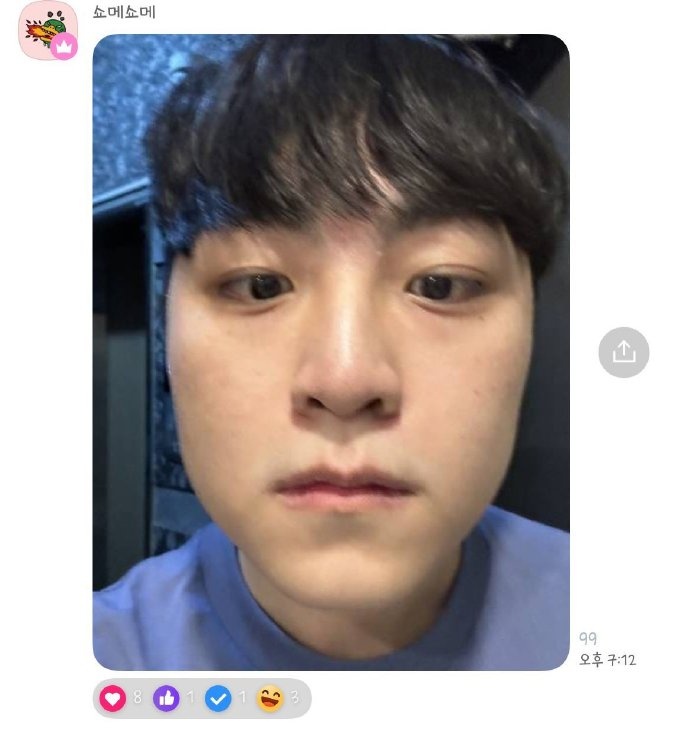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