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就是布谷鸟的鸣叫呵她的知识就是村前那条流不完的小河呀她的胸怀就是村后的深山哪她用老母鸡般的翅膀呵护着孩子们诗一般的年龄学校里飘出的悠悠钟声那是小村最甜美的音乐呵教室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那是村民们最甘醇的美酒呵村民们用孝敬长辈的赤诚喂养着乡村女教师他们期盼着她的粉笔能够画出精美的犁杖耕耘孩子们的未来收获沉甸甸的希望到后来孩子们抖动着坚硬的翅膀纷纷翻飞成思乡的风筝一端系在山村一端飘在山外
山在水中水在山中山水相映尽在云中山中有山水中有水山水相依尽在雨中是云不是云是雨不是雨云雨相融缭绕村中村在山中山在村中村山相抱拥入怀中一山又一山一村又一村山村相似刻在心中见山不是山见村不是村故乡相唤萦绕梦中
一杯酒能代表一颗心吗一切能在酒里吗隔着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仿佛隔着遥远的往事端起酒杯的时候恰好是揣起一颗冰冷的心仿佛那窗外的秋雨冷不防会钻进你的心底其实其实我也是窗外秋雨中最冰凉的一滴其实大家都想散席聚会只是一种无聊的游戏独自站在秋雨中你才会找到迷失的自己就把自己交给风吧交给窗外凄凉的雨滴大街上空空荡荡惟独出租车能为你导航把你送到梦里去
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你怀揣对光明的梦想奋不顾身地闯入一个明亮的房间事实上,追求光明的征途中处处布满陷阱不是每一次追寻都有收获不是每一次收获都有价值等到天亮你才发现其实光明就在自己的身后窗外阳光明媚那里有高山,河流,树木,水草还有你的亲人和朋友你迷途知返然而,在前途与现实之间已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你上下翻飞,左冲右突试图突出藩篱,回归现实然而,光明就在眼前却找不到任何出路后来在玻璃的夹缝里我发现了你金黄
有很多看不惯的事情从太阳底下逍遥而过我高昂着头颅把目光移向别处不让岩浆从体内迸出来当秋天屈从地弯下腰让寒风肆意地吹过来当身边的树木一棵棵倒下我才深深地打了一个寒颤我大声呼喊亲人和朋友的名字用歌声喊用生命喊却没有任何回声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世界;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题记第一章事故原委我是仁安小镇上的一名兽医,名字叫赵汉卿。自从我从事兽医这一行,镇上的人就直呼我“兽医”,反倒把我的真实名字忽略不提了。我最近摊上了一件事,是一件很窝火的事。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摊上这档子事,还真是让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去年春天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堂屋里吃早饭,突然从我家大门口径直走进来一个后生,在院子里他就喊:“哎—
冬季把小村雕刻成一朵朵雪白的馒头那尖利的北风从东刮到西从南刮到北搜刮着小村的草垛和屋顶炊烟袅袅升起雪白的馒头里静静地发酵着山村的童话故事
布谷鸟用婉转的歌喉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记忆当春风一阵强似一阵河岸上的垂柳已经抽芽小草悄然拱破湿土露出脑袋布谷鸟就叫起来了布谷鸟用单调的歌喉一遍一遍提醒着人们——播谷了,播谷了我们这些小孩伢子将露着棉絮的小袄扔在一边醉倒在湿漉漉的原野里父亲们扛着锄头吆着牛把一首首山歌播撒在山梁上母亲们聚在河边捶打着拆洗的被褥和村里面左邻右舍的新鲜事当布谷鸟掠过头顶她们高兴地竖起了耳朵听布谷鸟高一声低一声地叫
立春了春雨却没落下来被寒冷统治了一冬的城市在残雪中颤抖林立的烟囱以挺拔的气势掠夺着城市的天空垃圾袋像暴风雨中的海燕在半空高傲地飞翔鱼儿钻出墨绿色的水面绝望地望一眼过往的乌云人们缩着乌黑的脖子在尘土飞扬和汽车尾气中奔波春风带来了春的气息一场酸雨落下来鱼儿在水面上漂走了树枝不敢早早抽出嫩芽来就像人们缩了一冬的脖子虽然已是春天的阳光城市却在春风中瑟缩被污染的城市四季里都没有鸟儿的歌喉只有街头巷尾几株没皮
坐在三月的门槛等你等你细雨空朦中的一句甜言等你延展枝条上的一朵妩媚其实我在严寒的冬季就开始等你了摸摸下巴上的胡子才知道寂寞的冬季好长坐在三月的门槛等你收割完冬季一样长的胡子等你在三月的细雨里等你在绿色的声音里等你坐在三月的门槛眺望六月的原野
春暖花开时节,和煦的阳光照耀在这一片池塘上面。蛙声如潮,春风殆荡,好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青蛙们漂浮在碧青色的池塘上面,或蹲在飘摇的荷叶上,鼓动起硕大的蛙鼓,“咯咯咯咯”地赞美着春天。它们把爱的种子播撒在水草中间。这些种子,起初是一团一团的,粘稠状的,不久,便慢慢蠕动起来,长出一截黑黑的小尾巴,变成一只只可爱的小蝌蚪了。小蝌蚪们甩动着黑黑的小尾巴,在池塘里无忧无虑地上下翻动,活泼极了;一大群小蝌蚪聚
孟然钓鱼在县里很出名,每年的各种钓鱼比赛他都能取上名次。这当然与他的悟性有关,同时更与他的勤奋努力密不可分。他白天钓,夜里钓,风里钓,雨里钓,节假日钓,上班时钓……一心扑在钓鱼上。不幸的是,单位把他除名了。本来小日子过得就很拮据,这一来,就更苦不堪言了。妻子有了外遇,他不闻不问;女儿会考成绩全班倒数第二,他不闻不问。唯独把钓鱼的事牢牢地挂在心上。这一天,外出钓鱼的孟然很晚才回来。妻子狠狠地跟他吵了
经过职工群众的昼夜拼抢,水库大坝提前三天达到度大汛桩号。大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在工地调度室,管理局组织召开工程建设总结大会,总结前一段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大家都明显地累了,甚至都懒得互相打一个招呼。大家都在烟雾缭绕的调度室里东倒西歪地坐着,有几个角落甚至传出忽高忽低的呼噜声。管理局局长宋曦走进调度室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径直坐到主席台上,眼睛里布满血丝,一脸困倦的样子。他把秘书交给
寒冬还未退尽,春天却已到来。一阵阵湿热的春风吹进校园,将操场周围的柳条吹得暗绿,将满操场洁白的积雪融化得七零八落、残雪点点。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像鸟儿一样飞出了教学楼,他们追逐着,戏闹着,活像水皮子上一群撒欢儿的野鸭。不一会儿,铁锨清雪声、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响成一片。王小兵握紧的雪团带着淅淅沥沥的水滴从同学们的头顶上飞过,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玲子的背上。接着又一个雪团飞过来,玲子躲闪着,咯咯地笑着,嘴里高
英波坐在小板凳上,心事重重的样子。半个下午,她一直出神地望着江下那热火朝天的矿山工地。虽然她看不见孟春的影子,但她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心想,孟春今晚能不能来半拉山酒馆呢?半拉山酒馆建在半拉山的山腰上,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通往江下的工地。酒馆里的几个女招待员,个个长得水灵,而英波在里面又最拔尖儿。她白白净净的一张圆形脸,粉嘟嘟的,活像一个熟透了的桃子。她细眉大眼的,眼睛晶亮亮的放光,就像两颗会说话儿的
这天早晨,我们正在堂屋里吃早饭,突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喊:“兽医在家吗?——有活儿来了,请跟我走一趟。”我端着饭碗站起身,看见胡来走进来。他还是站在堂屋门口,搓着手说:“我家那头公牛的右后腿断了,想请你去看一看。”“怎么弄断的?”我问。胡来说:“是这么回事——昨天下午,我爹赶着牛去耕地,走到镇政府西面马路上的时候,后面开过来一辆吉普车,车上坐着镇长胡爱国。——你听说过吧,胡镇长在咱们镇上干了不到两年半
当天夜里,玉涛没有回来。第二天,玉涛还是没有回来。第三天,玉涛仍然没有回来。第四天下午,玉涛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浑身泥水从外面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狂饮了几杯凉开水,就一头倒在炕头上,呼呼大睡过去。大雨时断时续下了两天两夜,在玉涛回来的第三天下午才转为毛毛细雨,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我打了把雨伞,沿着亮马河堤岸往下游走去。这时候,亮马河里浊浪滚滚,一排排巨浪携裹着树枝、杂草、庄稼及死猪烂狗,以不可阻挡
大雨一阵连着一阵,没有停歇的意思,一直到傍晚还在哗哗地下着。秀枝用潮湿的柴火煮晚饭,弄得屋子里乌烟瘴气的,很是呛人。好不容易把晚饭做熟了,却忽然断电了,屋子里漆黑一片。我摸到打火机,照着微弱的光亮,从橱柜里翻出半根多年不用的蜡烛。蜡烛发出的豆大的光亮虽然也很微弱,但在这暴风骤雨之夜却给了我许多温暖和慰藉。正当我和秀枝在跳跃的烛光里吃晚饭的时候,从黑暗的雨幕里闯进来两个人影。在烛光的照射下,雨衣上的
中午时分,小镇上一片沉寂,一丝风也没有。人们发现,一片黑沉沉的乌云从北边的山岭和沟壑构成的锯齿形地平线上慢慢铺展开来,已经有一些短促的闪电倏然划过,但还听不见雷声。麻雀们从原野里飞回来,在树枝和房檐下焦躁地飞来飞去;鸡鸭鹅狗们也从外面的大街上陆续回到家里,在院子里唧唧喳喳地嬉闹着。不一会儿,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呼隆声就从天际滚过来了,带给小镇上的人们一种惶恐不安的信息。当地有古老谚语云:云彩向南,
当我一无所获地从镇政府办公楼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人从敞开的铁栅栏大门口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接着有一辆警车转着警灯响着警笛开进来,直奔政府家属住宅区方向去了。这时,从办公楼里跑出来几个干部,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干部神色慌张地说:“快过去看看,那边出人命了。”我跟着这几个干部快步来到镇政府家属住宅区,发现那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在两座楼中间的甬道上躺着一具女尸,地上淌了一大摊黑血。徐立安也
 纪录片《眼见为实》 圣枪哥一步之遥的遗憾
纪录片《眼见为实》 圣枪哥一步之遥的遗憾
 前LPL英文解说Kitty晒上海Major现场照:被导播拍到啦!!!
前LPL英文解说Kitty晒上海Major现场照:被导播拍到啦!!!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直接点赞!rita晒双城之战主题卫衣照片 黑白穿搭更显清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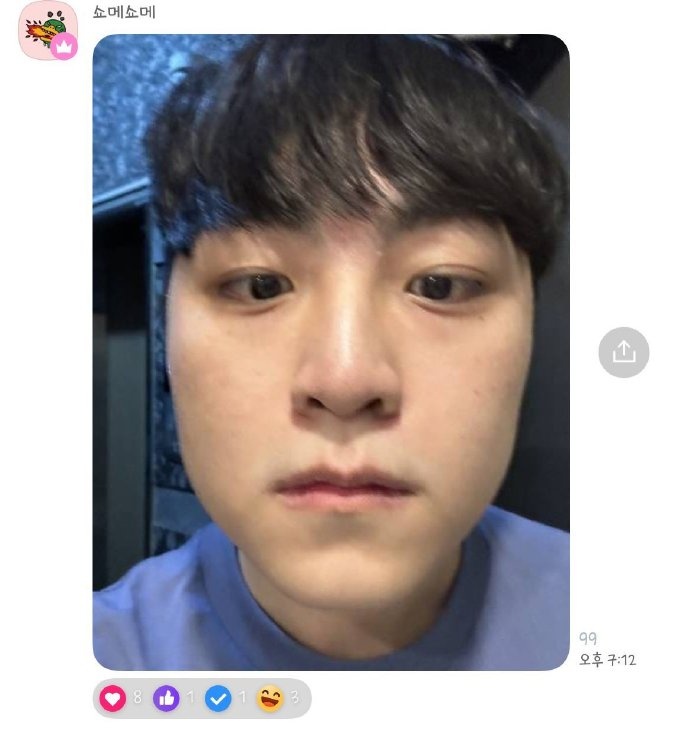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直男自拍?ShowMaker社交软件上分享直拍大头照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转行卖衣服了?无状态更新微博晒穿搭:主要是好天气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有点糙?网友发现:Zeus宣传片里举的HLE旗子上ID还是Doran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大家想看的不是这个!iG官方:下路Ahn正式离队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RNG欠薪让Ahn失业?爆料人调侃Ahn找队:蝴蝶效应 造化弄人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Leyan前女友晒照:低胸背心 天赋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