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作出决断和选择时,不被他人理解,就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孙权决定赤壁抗曹,除一、二人外,群臣均不理解。孙权的理由是,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早就想废掉汉朝自立;为复兴汉室,他与曹操势不两立。群臣以为,曹操毕竟打的是朝廷的旗号,归顺了曹操还不失封侯之位;冒险抗曹,如果失败,就是一败涂地,甚至性命不保;如此很是不值。其实孙权的心里话不好说出来。他真正的意图是与曹操相抗衡,以争霸天下,建立帝王之业。
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讲的“不争”并不是字面上的与世无争。他是企图通过“不争”来取得比争更好的结果。“不争”是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争”是为了从根本上争胜。老子认为“不争”是获胜的有效途径。他的“不争”是高明的争、高级形态的争,是不争之争。(李光福:论老子独特的人生进取观,南开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第92~100页)按照这一看法,老子不争是假,争才是真。这就完全是谋士之道,毫无隐士之道;
老子有一段“小国寡民”的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实际上这就是老子设想的,在无欲无知状态下合于道的社会生活。有论者评论这段话说:“这不过是老子学派记录的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从中不能看出他们的理想就是所谓‘小国寡
圣人,或“古之善为道者”,在对待老百姓上面,是“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是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65章)论者多认为这体现了老子反人民的立场。如有论者列举老子的一些言论后指出:“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愚民”,“《道德经》反对一切有为的追求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无为的方法,实现君主顺利统治,欲民之愚昧无知而使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因此,《道德经》
一方面是统治者过着奢侈的反自然的生活,另一方面,一般老百姓想要过那种“实其腹、强其骨”的生活而不可得。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77章)依据道的精神,“损有余而补不足”,才能解决这一社会矛盾。首先是要求统治者按照不欲、无欲、寡欲的原则去做。老子提出一个口号就是知足。“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
老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将无欲、不欲或寡欲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他说:治国者的治国之道是“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第37章》,以下只注章数)他还说,“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这里的朴或素,是指合乎“道”的人的“自然”本性。这种无欲,圣人首先是从自己要求起。“圣人云:‘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老子还具体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
新年伊始,尼采的病情有了突变。1月3日上午,尼采在住处看到一个马车夫使劲抽打他的马,就跑出去抱住马的脖子,结果摔倒在地。房东把他送回房间。从这一天开始,尼采出现明显的精神错乱症状。以后几天,尼采几乎给他的每一个朋友都写了信。从这些信上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尼采疯了!给加斯特的是一张明信片:“我的音乐大师彼得:给我唱一支新歌吧:世界光明,万物欢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给勃兰兑斯的信没贴邮票,也没有详
从尼采在1888年写的几部作品看,他的观点是明确的,论述的问题也很集中,既有最新思索的结果,又有对以前重要思想的承绪。他的创作状态极佳,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在都灵期间。他对加斯特说:“我心情很好,从早到晚地工作着──我正在写一本有关音乐的小册子──我像一个半神半人那样地消化,不管马车夜间行驶的声音怎样嘈杂,我都能安然酣睡:对尼采来说,都灵有那么多特别合适的征兆。”但另一方面,他也时时有一种烦躁不安
自从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的精神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用他的话来说是由肯定的阶段进入否定的阶段,“现在不再由查拉图斯特拉说话,而是由我直接来说话。”而《善恶的彼岸》只是这一否定工作的序曲。对于这整个工作,尼采给予它一个名称叫做“重估一切价值”。他1888年完成的几本书,还有自1887年以来的大量未完成稿,都是在这个总目标下的具体成果。在这些著述中,尼采着墨最多、论述最力的问题是生命
1887年秋,尼采正准备去威尼斯,9月,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杜森同妻子一起来访。这时杜森刚刚获得哲学教授的职位。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在杜森看来,尼采的变化很大。以前的尼采,总是一副高傲优雅的姿态,走路十分矫健有力,说话流畅生动。现在的尼采显得十分疲弱,走起路来有点朝一方倾斜,好象是被拖着走,神情有些迟钝,说话也结结巴巴的,也许这是长期不跟人交谈造成的结果。尼采把客人带到他最喜爱呆的地方,那是一块紧靠
(这是好友晓江对我的《生死对话录》的回应。——黄忠晶于2019-5-18)忠晶兄,发来的文章均己拜读,生与死的对话还不止一次读过,只是,我很少去想、去提这个话题,对于死亡,我很淡然、很漠然。我跟你一样,在上学前经历过一次死亡。我在池塘边抓蜻蜓一不小心掉下去了,好像沉下去了,同村有个姐姐因小儿麻痹症不能出工,只能在家料理家务,她去池塘边洗衣服,看到水中漂着一条红绸子,她一提就提出来一个小孩,那绸子是
决断也就是作出选择。人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在作出选择时,我们处于一种两难境况:我们不得不时时作出选择,但我们在选择时又没有实在的依据可循。我们的选择是根据一定的原则或标准作出的。人们通常以为它们是可观的、带普遍真理性的,但仔细一想,这些原则或标准仍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孙权在面临是否送儿子作人质的选择时,他的原则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江东
在孙权身上,交织着两种似乎彼此矛盾的思想和心态,一种是“天下舍我其谁”,一种是“我本平常”。他接任江东领袖之时,就有称霸天下之心。鲁肃秘说帝王之业,甚合他的心意,所以他不顾张昭的反对而重用鲁肃。同时他对鲁肃表示,这个帝王之业还不是他能做到的,他只是希望能把江东治理好。他也从不对其他臣下谈及他的这个志向。直到几十年以后,他已成就了帝王之业,他才谈到鲁肃当年的劝说,把这定为鲁肃的首功。孙权给人的感觉是
按小说《三国演义》给人的印象,孙权的特点就是会用人,此外再无其它能耐。用周瑜,则一切都听周瑜的;用吕蒙,则一切都要靠吕蒙;用陆逊,则一切全凭陆逊作主。……他自己似乎是个并无什么主见的人,军国大事全由别人决断。果能如此,他这个当领袖的,可就轻松得很了。果能如此,他这个当领袖的,也就跟一个傀儡没有什么区别了。实际上孙权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敢于决断、明于决断的雄略之主。其实用人本身就是一种决断:用这
写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一生中事业的肯定部分已经完成,现在他开始做事业中的否定部分,即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1885年6月尼采离开威尼斯到西尔斯─玛丽亚,着手写一本新书《善恶的彼岸》,其核心是对现代科学、现代艺术以及现代政治的批判,同时也指出与现代人相反的形态──一种高贵的而又积极的人的形态。这书可以看作是他拟定要完成的庞大工程《重估一切价值》的导言。9月,尼采回到瑙姆堡,然后在莱比锡、慕
查拉图斯特拉本来是古代波斯传说中的一个神,一手握蛇,一手举鹰。蛇象征着人生的永恒轮回,而鹰象征着充满创造力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以鹰来制服蛇,就是要用超人来战胜人生的永恒轮回。这个形象想必是尼采在经过许多次思索后偶然获得的;但一旦获得,由于它正可十分贴切地表达他的思想,于是尼采自身也就幻化为两个人。其后的一切都是他同自己创造的人物的对话。尼采选择这个人物并不完全偶然。由于不愿意同基督教的历史渊源发生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无为而无以为”与“无为而无不为”的区别。有论者提出,“道家‘无为’理论,其基点在于强调人不应当刻意追求,甚至连想都不要想,而应当让一切都随顺自然。这在老子早期的理论中称为‘无以为’。老子后期的哲学思想适应了社会形势需要,于‘无为’理论中加上了积极进取的内容,提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命题,将随顺自然的命题加以改变,变为随心所欲,无所不为。”(晁福林:试论先秦道家“无为”思想的历
老子还有其它一些重要言论,虽然没有用“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字眼,但其意思是一样的。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5章》,以下只注章数)刍狗,用草扎的狗,供祭祀用,用毕即扔掉。天地不表示对万物的爱护,而让它们自生自灭。圣人不表示对百姓的爱护,而他们自生自灭。这里天地、圣人贯彻的都是道的精神。不表示特别钟爱某物,是无为,让其自生自灭,是“自然”。虽然人
与“道法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37章》,以下只注章数)的思想。这意思是,道自身总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没有什么要特别去做的,而天地万物却因为道而生成、活动、变化,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老子说:“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37章)治国者若能依据“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务也就会“自化”——仿佛是各自顺其自然地完成了。类似的话还有
对“百姓皆谓我自然。”一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老百姓都认为是自己就这样做成的”,即“百姓皆谓‘我自然’”,似乎与治国者无关;一种是“老百姓认为治国者是自己这样做成的”,即“百姓皆谓我‘自然’”(这里“我”是治国者的口气),“自然”是百姓对治国者行为的评价。持第二种观点的论者理由是,第一种理解不符合《老子》全文中“自然”的基本思想,按照这种理解,自然只是百姓自认为如此的一种陈述;但事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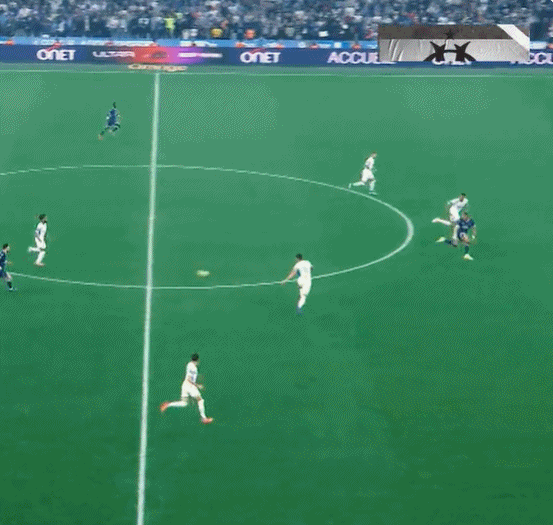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从马赛防到阿森纳!论单防姆巴佩,萨利巴可太有经验了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2025LPL第二赛段趣味数据:时隔2211天,IG再次丝血翻盘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U21联赛第3轮:上海申花U21客场0-0战平浙江U21,三轮联赛积7分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天选的对线克星?TheShy职业生涯中疑似被Ale单杀了16次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法甲彩经:大巴黎争赛季不败夺冠 马赛主场大捷?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天工CEO:本届机器人半马夺冠具有里程碑意义,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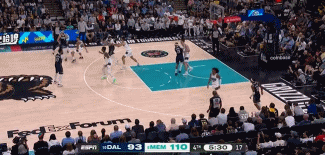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玩起来了!康查尔前场1打0玩打板妙传 小贾伦跟进暴扣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iG整活:逮捕一位身负1500条“人命”、鳄贯满盈的冷酷杀手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阿德巴约谈首轮打骑士:关键在于怎么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